“新王宫”是海龙囤内最大的建筑群,有闭合垣墙环绕,面积达1.8万平方米,内有建筑30组(F1~F30)。建筑整体坐西南向东北,有清晰的中轴线,并大致形成“三进三路”的格局,自前而后逐级向上抬升,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图一)。文献中又称其为“衙”“衙院”“衙宇”“衙舍”等,知其应为杨氏土司的衙署遗址。虽无具体文献记载,但结合明代典章制度以及现存土司衙署的一般格局,可以推定“新王宫”大致存在治事之所、宴息娱乐之所、礼仪宣教之所等不同功能空间。土司衙署的格局,受到堪舆之术、典章制度、礼仪规范以及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影响。
一、治事之所
治事之所,分布于中轴线及其近旁,包括土司治事之所与吏攒办事之所等。这里是土司通过司法、礼仪、机制、策略与传统等进行权力运作的空间,彰显了严密的空间秩序与政治礼仪,某种意义上是土司统治合法性的政治表达,其整体格局与同一时期的府县衙署和土司衙署并无明显区别。房屋的规制,明代典章制度有明确规定。《明会典·房屋器用等第》记载:
凡房屋,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官员盖造房屋,并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绘画藻井,其楼房不系重檐之列,听从自便。
公侯,前厅七间或五间,两厦九架,造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屋三间五架,门用金漆及兽面摆锡环,家庙三间五架。俱用黑板瓦盖,屋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栱、檐桷用彩色绘饰,窗、枋、柱用金漆或黑油饰。其余廊庑、库厨、从屋等房,从宜盖造,俱不得过五间七架。
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许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桷用青碧绘饰,门屋三间五架,门用绿油及兽面摆锡环。
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桷用青碧绘饰,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摆锡环。
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止用土黄刷饰,正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
一品官房舍,除正厅外,其余房舍许从宜盖造,比正屋制度,务要减小,不许太过,其门窗、户牖并不许用朱红油漆。
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及彩色妆饰。[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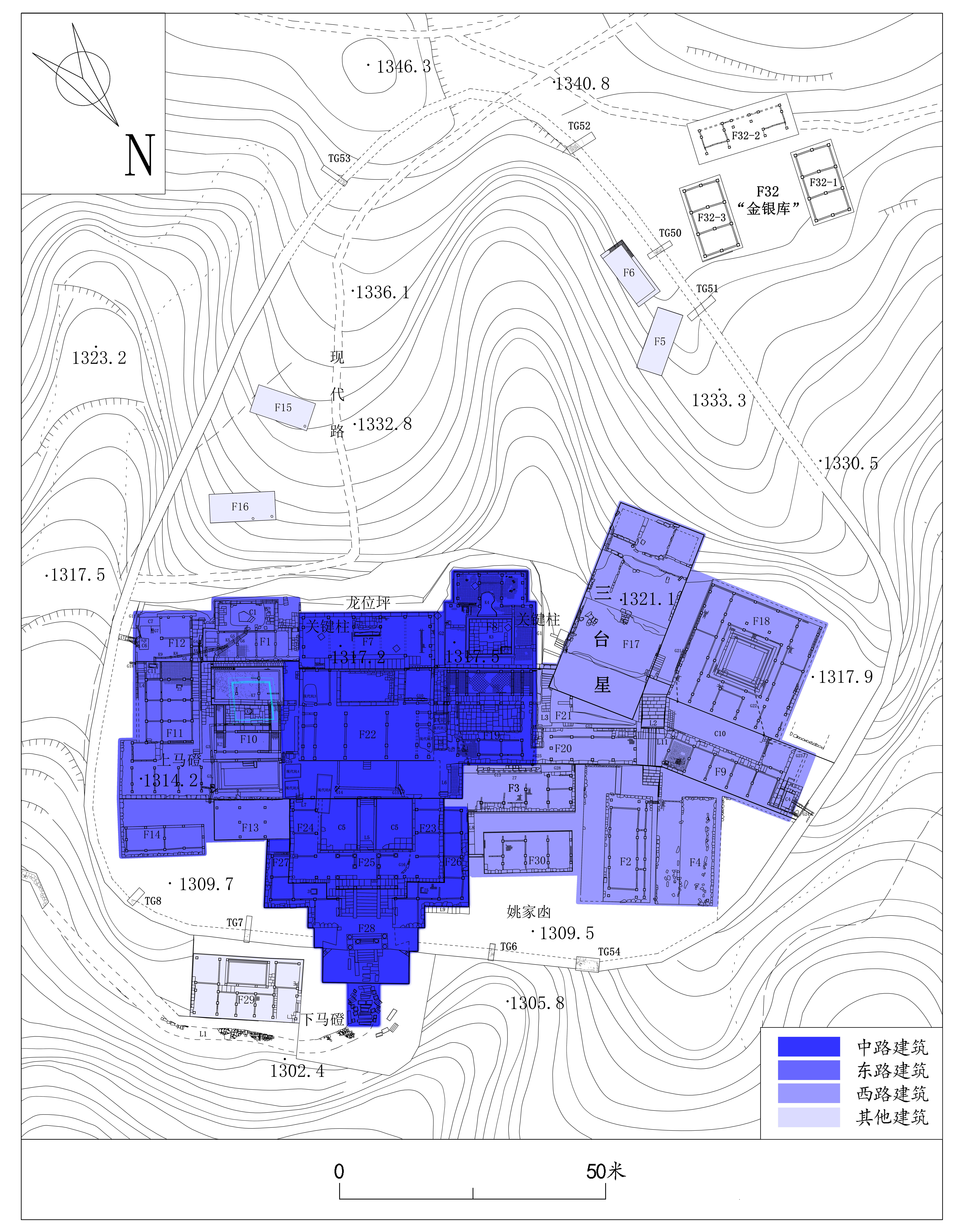
图一 海龙囤“新王宫”遗址平面图
上文对厅堂与正门的开间、进深及其屋面装饰,以及梁、栋、门、檐角的装饰做了细致的规定,依官阶依次递减,秩序井然。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属从三品,按制,其厅堂五间七架,屋脊可用瓦兽,梁栋等装饰色为青碧色,正门三间三架,锡环与黑油装饰。“新王宫”大堂(F22)、二堂(F7)均五间七架。大门(F28)、仪门(F25)均三间三架,但仪门左右另设耳门,前有廊。整体而言,建筑规制与主人身份相符,并未僭越。
参照明清土司衙署与府县衙署,居中的大堂(F22)为土司治事之所,是衙署的中心所在。其前两厢(F23、F24)各三间,为六房,系吏攒办事之所。据河南内乡县衙,当按“左文右武”排列,即左为吏、户、礼,右为兵、刑、工。土司治下类似的设置,见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的记载:成化十四年(1478),“杨爱因见各里土民不谙书办,不合违例,将市民姚鉴佥充本司兵房典吏,王裕佥充本司刑房典吏,何文佥充本司户房典吏,杨仑佥充本司礼房令史”[2]。《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也提到囤上常设有“书吏”,亦当在此办公。刑事审理,是衙署空间最常见、最频繁的政治实践运作,土司衙署亦然。云南南甸宣抚司衙署的公堂(大堂)即是土司升堂办案处。前书有记成化十二年(1476),“杨辉令人叫韩瑄到司,唱令失记名皂隶,将韩瑄责打六十大棍才扶回家”,使其因伤而死。这类活动,应在播州城内的宣慰司司治的中庭(忠孝堂)进行的,“新王宫”内大堂(F22)就是海龙囤上的“忠孝堂”。相应的,土司衙署内应有监狱的设置,嘉靖《思南府志》所载的水德江长官司、蛮夷长官司、沿河祐溪长官司、朗溪蛮夷长官司等四座明代土司衙署,规模虽小,但均建有监房,且皆置于右侧。俗谓“东掌生,西掌死”。“新王宫”内有“水牢”的地名,虽发掘揭示其并非监房而系一条地下通道(L2),但暗示“新王宫”内应有监房的设置。参之前述四长官司署,“新王宫”内监房亦应在右路,则偏处右路前端且相对独立的F13、F14为监房的可能性最大。
二堂(F7)处于中轴线末端,五间七架。因明间有后期供佛用须弥座石台,民间俗称“龙位坪”。其前两厢仅面阔一间,当为连通大堂与二堂的穿堂,从天井左右两侧廊道尽头未见石质踏步看,当有木质楼梯设于两厢内,上抵F7内。广西忻城莫土司衙署的二堂是土司内部议事之所,土司于此处理日常事务。而内乡县衙的二堂,则是知县预审案件及大堂审案时退思、小憩之所。“新王宫”二堂功能应与之相当,乃土司处理内务及休憩之地。
土司杨应龙手书的《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显示,土司不在囤时,由“总管”总理囤上事务,并设“总管厅”,负责“上名、应役”及收缴与发放出入各关的凭证“水帖”。中路既为土司治事之所,则大堂左侧的F19即可能为“总管厅”。F19为一组合院式建筑,由正房、倒座、天井与回廊组成,是通往左路建筑群的中枢,且做工考究,以经打磨的方砖墁地,下铺河沙。前述明代四长官司署中“吏目厅”“幕厅”等辅佐土司工作的吏目治事之所即均设在大堂之左,内乡县衙亦以左为尊。
大堂(F22)右侧的F10,是一组合院式建筑,由两院、正房、倒座和回廊组成,正房有精美石窗装饰,倒座前回廊立有石望柱。正房墙体厚实,仅于左前设单门出入。其内出土骨质戥子、有清晰人工切割痕的鹿角等遗物。
据此推测F10可能为土司储存财物的府库类建筑。《平播全书·破囤塘报》记:六月初六日,明军破囤而入,“随将应龙衙舍府库,合兵围之”[3]。将衙舍与府库并提,府库应在衙署内。有趣的是,F10正房后期曾屡遭盗扰,遗留较多坑穴,地面铺砖均已无存,部分石础与地栿下陷移位。这一情况并不见于其他建筑,或即因其内储有财物故。
大门右前的F29是一组相对独立的合院式建筑,由倒座、两厢和天井组成,偏处“新王宫”垣墙之外、主道近旁。内出石锅圈等遗物。房址所在地,民间俗称“下马磴”,意指人员在此停歇、下马。该俗名与房址位置暗含迎宾、看守之意。毕节大屯土司庄园于其右路前端设有客房,云南武定慕连土司署亦在右路前端设客房,明代府廨的客舍(寅宾馆)亦多置于右前[4]。基于此,F29较可能即客舍。另据《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新王宫”还专设“守衙小童”与“打扫户”,负责衙署看护与卫生,这些人员可能即住在衙署之外的客舍中,实现对衙署“守”与“扫”的日常维护。
据《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囤上另设有总领、把总、提调、总旗、小旗、军士、苗军、驻囤医生、匠作、住持人等。总领大约亦在大堂前六房办事,把总、提调、总旗、军士、苗军等,应驻守于各关隘,如龙凤关设有把总,万安关设提调。匠作负责施工,驻囤医生或主要负责施工人员伤情处理,住持人则居其所主持的庙宇内。“新王宫”后端沿垣墙分布的F5、F6、F15与F16,因地处后关入囤之要冲,具有明显的防御性,亦当有军士、苗军把守。
二、宴息娱乐之所
宴息娱乐之所,指土司及其家人与吏目在衙署内的居住、宴饮与娱乐的场所。
一般而言,无论府县衙署还是土司衙署,知府、知县与土司宅多位于中轴线后端,少量居于一侧,如甘肃鲁土司衙署中土司宅居左路,朗溪蛮夷长官司署中正长官田氏宅亦在左路。
《平播全书·叙功疏》记载:六月初六日,明军破囤前夕,杨应龙“入卧房将门钉闭,举火烧房,同爱妾周氏、何氏自缢死”,吴广等“至后房,破门寻见酋尸,急出诸烈焰中。须臾,火烧楼房一空”[5]。应龙自缢的“卧房”即后来寻见尸首的“后房”,可见土司卧房居于后端。按衙署前衙后邸的一般布局,审以“新王宫”建筑格局,在中轴线近旁又居其后的,唯有F8一组建筑。这是一组合院式建筑,由三开的正房、两厢、天井与前廊组成,右前有木栈道跨G2与二堂(F7)相接,反映其关联性。F8台基较F7高出约0.3米。当土司于二堂处理完公务后,可便利退居F8内休憩。因此,F8当即前述“后房”与“卧房”,为土司内宅,是其与妻妾的居所。天井内出土石砚台、青铜象棋子(仕)等遗物,表明F8除卧房外,可能还兼有“书房”的功用,即《严禁碑》所谓“但恐亲临本囤,跟随一应人役,书房听点题单,预发龙凤关,查点进出”者。F8内有砖砌灶台1个(Z1),叠于F8正房的地栿石上,靠压的正房檐墙杂乱无序,当为后期遗存。
前述永登鲁土司署、朗溪蛮夷长官司署中,土司宅均居左路,结合内乡县衙除中轴线外“以左为尊”的特点,有理由认为“新王宫”左路的姚家凼一带(F2~F4、F30)应即土司家人的居所。据《平播全书·献俘疏》,应龙有四妻(正妻张氏早年为应龙所杀,次为田氏,再为与其自缢于卧房的何、周二氏)八子(次子可栋早年死于重庆)二孙三女[6]。妻妾与土司共居内宅(F8),其余家人可能即住上述四房内。甚至“姚家凼”一名或系“杨家凼”之讹,意为杨家所住之地。
思南明代四长官司署中,均考虑了“吏舍”,左右不拘。结合“新王宫”格局,六房台基下的东西配房(F26、F27)可能即“吏目”住所。配房呈曲尺形,环六房(F23、F24)与仪门(F25)而建,以其台基为配房后墙,墙上留孔,横梁插于其内。配房于仪门台阶下设对称入口,并各置一砖砌灶台(Z5、Z6),显系生活区。于六房办公的吏目,出仪门即可进入此间,往返便利。
右路中央的F11,系一组纵横交错的“L”形建筑,当地民间俗谓“上马磴”。纵向者四开,左右二列并置;右列稍窄,后端设水池(C11),水源以暗沟引自C1内;左列七架,自北而南第二间内有砖砌灶台(Z3),表明其系生活区。横向者三开,右设门房以通L4(上达右路建筑后端)。结合“上马磴”的俗称,此或系马厩及用人居所,纵向者为居所,横向者为马厩。
左路最西侧的F9,该侧五间三架,紧邻水池(C10)。已发掘的东稍间设灶台(Z2)及方形石水槽。内出瓷片万余片,分属近500件器物个体,其中可复原者达143件,且不乏官样瓷器。另有铁锅等遗物。所有证据均指向,这是一组厨房。官样瓷器的发现,进一步表明使用者身份不凡。该厨房可能与家庙相关,亦可能与土司宴饮相关。F9东侧紧邻F20,为四间三架长房,前设石铺道路(L11),右连F19左通F9。因邻厨房(F9),F20的功能或同于忻城莫土司衙署大堂右侧的东花厅,为接待外来官员与宾客的宴会厅。
右路后端有C1、F1与F12,前有L4与之连通。F1五间三架,与二堂(F7)并列,东设门房与L4通,东梢间内横置巨石一方。1999年试掘时,曾于此获围棋子数枚。F1北接C1,池底墁石,后置加工规整的巨石为影壁,做工考究。水尤清冽,至今不涸,又以暗沟引往C11内饮用。池西与二堂(F7)之间形成小型庭院(设门出入),院与池相接一侧垒有砖墙,墙头拐角处以合角吻装饰。池东的F12建于基岩之上,三间三架,但开间狭小,当系亭榭建筑。结合景观与所出遗物,这里当系一处宴游之地,扮演着后花园的角色。F1台基较F7低约0.15米,可惜据目前所遗残痕无法判断F1与二堂(F7)之间是否有路相通,从二堂(F7)可与左侧卧房(F8)相通看,亦应有路通向与F8大致呈对称分布的F1(并C1)。如此,土司公务之余便可退居其间宴饮游乐,亦可为其在紧急情况下从二堂逃逸提供方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左路后端的F18,这是一组四合院式建筑,由五间七架的正房与倒座(亦不排除中央三间打通呈明五暗三格局的可能)、三间三架的左右两厢、中央天井及其四周廊道组成。与衙署内其余建筑天井下沉为池状不同,F18中央天井向上凸起,台面高出周围建筑的室内地面15~25厘米,四周设排水沟。特殊的结构表明天井可能有着特殊的用途,或系一处仪式展演与戏曲表演的舞台,向上凸起的天井便于观者环坐四周观瞻。
播州境内,戏台与戏曲表演的场景最早见于赵家坝杨氏第20世土司杨元鼎(?~1371)夫妇合葬墓的石刻中,因葬于明初故仍保留元代墓葬的特点。该墓男女两室的左右龛内,左雕乐舞,右为奉食,男墓均男子,女墓均女子。人物皆处在形如戏台的建筑(即勾栏)下,作面向后龛的墓主人像徐徐行进状。男墓左龛九男子,所奏乐器可辨者有琵琶、拍板、横笛和胡琴等。女墓八女子,奏琵琶、横笛和笙等;前导一人手持曲首杖,上有羽状装饰,或即《宋史·乐志》所谓“执麾人”[7]。另据《勘处播州事情疏》记载:明成化年间,陕西乐户刘寿、刘鉴、郭福亮、张顺等“因本处艰难”,逃来播州“趁食住过”。而后,杨友诬宣慰使杨爱“使抄捉良民庞兆期女胜真、福真等一百余名充女乐,令乐户刘寿教习杂剧”,后经查明杨爱令刘寿“教习杂剧是实,并无抄札良民妇女充女乐”事。因诬告事宜,成化二十二年(1486)“有参政谢士元、都指挥杨纲、副使翟庭蕙前来体勘”,七月初九日三人“同到杨爱家看祖训碑。杨爱安排筵席相待,令人唤乐户刘鉴、郭福亮,又各不合依听到伊家弹唱”[8]。杨爱家即播州城内宣慰使司衙署,所记并未说明弹唱是否在戏台进行,但反映了杂剧表演之风在播州流行的盛况。历代土司受其浸染,当以之为乐事。这一风气可能影响到海龙囤上衙署的布局。
而在土司辖境的特定空间进行仪式的展演以达教化之功,播州城有农历七月十二的“迎赛壁山土主”仪式,文庙前大街似是展演的主要场所,每年依例进行。活动中,播州军民“装扮义夫节妇过”,既喧嚣又严肃。前述来播体勘的三位明政府官员因在文庙仪门下坐看,又欲饮酒,“殊失表率之道”而受责罚[9]。这实际上是一场祭祀壁山神赵延之的活动,除求得“雨旸应祷”的心理慰藉外,还是一个宣扬教化的重要场域。以戏台为载体,通过仪式的展演和戏曲的表演,既可娱神又可娱人。云南南甸宣抚司署的左路建筑中即有戏楼的设置。清容美土司境内司治及各行署多设戏台,土司田九峰还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延请戏曲作家顾彩客居土辖境。如其宣慰司治衙署大堂之后的楼中设戏厅,行署平山爵府的关公庙前亦设戏楼,关公诞辰日(农历五月十三日)还“演戏于细柳城之庙楼”,并大会宾客,又“具朝服设祭”,乡民有百里来会者[10]。在关公庙前设戏楼,以及细柳城庙楼的戏剧表演,人神皆娱。衙署内设戏台,既是土司个性的表达,又是娱乐与教化的需要。
鉴于“新王宫”内F18天井高耸的特殊结构,加以处在家庙(F17)近旁的特殊空间,参之前例并结合播州戏曲之风颇盛的历史背景,其为戏楼的可能性较大。惜乎未进行全面揭示而取得更多的证据,故以上推测是否正确,尚留待未来的田野工作予以检视。
三、礼仪宣教之所:兼说杨氏家庙
前述戏台已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但表现得更为突出的当属家庙。祠堂祭祀本身就是封建礼法的一部分,朱熹(1130~1200)在《家礼》的开篇便讲祠堂,并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方向的取定,“凡屋之制,不问何向背,但以前为南,后为北,左为东,右为西,后皆效此”,即不论向背,一律视为坐北朝南。“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又规定,“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非嫡长子,则不敢祭其父”[11]。于播州杨氏而言,继承土司职位的嫡长子便是“宗子”,族人须接受其治理,并由其主持祖先祭祀的仪式。家庙与祠堂性质相同,但也有所区别。据《明会典》,品官称“家庙”,庶民为“祠堂”,且因“国朝品官庙制未定,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12]。因此朱子《家礼》于明一代有广泛影响,于播州杨氏亦然。其“土司”诸墓中,由宋至明,墓志铭从置于墓中到置于墓外的变化,即是受《家礼》将志石“埋之圹前近地面三四尺间,盖虑异时陵谷变迁,或误为人所动,而此石先见,则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为掩之也”[13]等要求影响的结果。
播州杨氏家庙的营建,始于第13世杨粲主播时。据元人程钜夫(1249~1318)撰于大德七年(1303)的《忠烈庙碑》记载:“嘉定六年(1213),高祖忠烈公(按即杨粲)始考典礼,建家庙,以祀五世。奉太师公(按即杨端)为始祖,百世不迁,余则有夹室以奉祧主”。至“咸淳四年(1268),考惠敏公(按即杨邦宪)又请于朝,锡今庙号(按即忠烈庙),刻家训(按即宋濂《杨氏家传》所记‘家训十条’)于石榜,崇孝于楼”。杨粲不仅建了家庙,还开启了对华夏礼仪的全面吸纳,出土的《杨粲墓志铭》即记其“讲诸侯五月而葬之礼,棺椁制度,焕然鼎新”[14]。而尊杨端为始祖反映了杨粲“改制”应还包括对其祖源记忆的重构,杨氏从此由本土土著转变为“太原诗礼旧家”[15]。杨氏的家谱,此时可能已经出现。至元二十八年(1291)杨文妻田氏墓志铭中有“穹爵修门,见之家谱”句,是宋元之际家谱已在黔北流行的信号[16]。杨氏超越空间(从太原到播州)的祖源构建,是华夏“英雄徙边记”的另一案例[17],通过寻得或假借一个华夏祖先传说而实现华夏化,是华夏边缘人群的一种普遍策略[18]。这一策略,使得杨氏成为异于周边“夷陬”的华夏“诗礼旧家”,故而拒绝与水西安氏土司(彝族)通婚。杨粲的举措,对播州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纷纷宣称其华夏身份。如宣慰使同知罗氏亦称其先为太原人,且先杨氏而入播;令狐、成、赵、谢等八姓则系太原人杨端的同乡;播州长官司王氏亦从太原入播;真州长官郑氏则为唐宰相郑畋之后云云[19]。足见华夏边缘人群对其所宣称的华夏祖源的倚重,家族血缘记忆终助其在蛮夷之地构建起复杂的社会网络,从而强化了其统治力量与统治的合法性。
据《杨文神道碑》,杨文主播时,为先父杨价请命于朝,宋廷“赐庙忠显”。是价先受赐(杨文于1265年辞世),而粲后赐(1268)。《杨铿墓志铭》称其祖“有封公、封侯伯者,有赐庙、赐食封者”,将“赐庙”与封公侯并置,可见所谓“赐庙忠烈”或“赐庙忠显”与杨文自己“谥崇德”一样,乃朝廷于其死后所赐美名,而非专为其另建祖庙。《忠烈庙碑》即径称“锡今庙号”(忠烈),明确其系“庙号”,与“谥号”相类。《杨粲墓志铭》称粲“建家庙,以祀五世”,而端为始祖“百世不迁,余则有夹室以奉祧主”,则“五世”当为始祖、高祖、曾祖、祖、父,各置其神主(牌位)或遗像于家庙中。
杨粲兴建家庙,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宗法之制,虽在商周即已流行,但随科举制的推行,于唐代出现衰落的迹象。宋初,官员并无家庙,四时祭祀只在住宅内举行。12世纪初,宋徽宗“徇流俗之情”,允许节度使以上官僚祭五世祖先,文武升朝官祭三世,其余小官和士庶人许祭二世,庙址设在私宅内的左面,或住宅外侧。家庙于是开始流行。理学家程颐(1033~1107)并不够祭五世祖的条件,却私自实行,民间僭越之举亦很普遍[20]。13世纪初主播的杨粲生前官至忠州防御使,按制亦不能祀五世,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建家庙而祀五世。
杨粲创建的杨氏家庙,应设于播州城内衙署的左路。前揭《忠烈庙碑》记杨邦宪(1242~1285)请命于朝,“锡今庙号,刻家训于石榜,崇孝于楼”,所谓“家训”应即宋濂《杨氏家传》所记“家训十条”,为“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佞,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据此可知,石碑立于家庙内。《勘处播州事情疏》记成化二十二年(1486)七月初九日,四川都布按三司官员“翟庭蕙与杨纲、谢士元同到杨爱家看祖训碑”。结合同书所记,可知所谓“杨爱家”即播州宣慰使司衙署。据此,杨氏家庙设于衙署之内。又《杨铿墓志铭》记:铿主播时,“冠、婚、丧、祭,一遵古典。大修祖庙,増祭器□□□□传,置杠梁,及所居第宅左旁,缉而一新之瑎庭”。可知家庙(祖庙)位于“所居第宅左旁”,即衙署左路。铭文称“大修祖庙”而非“新建”,是大修乃于已有家庙的基础上进行,并增设了祭器。其家庙的大致格局,据《勘处播州事情疏》记载:明政府官员在“杨爱住宅内看得”,“中庭扁作忠孝堂”,“其祖先堂承恩堂并小厅左右角门,有飞檐转角”[21]。此“祖先堂”即杨氏家庙,名曰“承恩堂”,而“杨爱住宅内”的“忠孝堂”为衙署正堂。该记载进一步表明杨氏家庙设于衙署之内,且其格局应是承恩堂居中,左右有小厅,设角门,屋面结构为“飞檐转角”。综上,自杨粲首创至杨铿大修,杨氏家庙俱在衙署之左,合于宋廷的规定,亦与朱子《家礼》的要求一致(立祠堂于正寝之左)。
回到“新王宫”,这所由杨应龙所创建的“以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的土司衙署,在布局上多取法于其播州城内宣慰司司治,亦可能在衙内设家庙,并置于正寝之左。“新王宫”内符合这一条件的有F9、F17与F18三座房址,且三房在空间与朝向上自成一体。空间上,居于左路建筑后端的高台上;朝向上,为54°,与中轴线建筑形成夹角(38°),这样的处理当系有意为之。彼此间的叠压或靠压关系显示,三座房址形成的整体建筑,相对关系上略早于其他建筑。此与朱子“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的要求契合。拆分来看,前文已推测F9为厨房,F18为戏楼,那么最可能为家庙的便只有F17了。F17建于独立的高台之上,自前而后形成五级平台,当地称“三台星”,不像民间随口而呼,可能为故老相传并潜在一些重要信息。三台星,是中国古代的星辰司命信仰之一,与道教关系密切,并将之升格为星君,“上台虚精开德星君,中台六淳司空星君,下台曲生司禄星君”[22]。各星司职,据《晋书·天文志》:“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次二星为中台,为司中,主宗室。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主兵,所以昭德塞违也。又曰三台为天阶,太一蹑以上下。一曰泰阶。上阶,上星为天子,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士,下星为庶人:所以和阴阳而理万物也。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变则占其人。”[23]说法不一,但中台“主宗室”,“三台为天阶,太一蹑以上下”等认识,使家庙与三台星之间产生了可能的关联,不过仍需更多证据支持。播州杨氏对占星术的重视,已有先例。据《勘处播州事情疏》记载:明成化间,江西人曾循道入播,只因“访得曾循道能观天象,暗晓兵机,迎请到州,拜作军师,日看兵书,夜观星斗”[24]。“三台星”(F17)建于五级平台之上,前台高峻,道自左右两侧对称而入,径至第二级平台,右路(L3)在入口之外另设门道。其左右两侧起砌山墙,石脚呈枭混线,颇考究。中央设踏步,拾级而上。从残存的迹象看,末端正房三开(第五级平台),前设月台(第四级平台);台下为两厢(第三级平台);再前为倒座(第二级平台),第一级平台应为庭院。这一格局,与《家礼》祠堂“三间”,“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的要求大致吻合。亦与播州宣慰司衙署内家庙“承恩堂”居中,左右设小厅的布局相似。又“神厨于其东”,因坐北向南,东即左,确定为厨房的F9恰在F17之东(左),应非巧合,而表明F9可能亦作神厨之用。居其左侧的F18,若确为戏楼,则宛若前述容美土司于关公庙旁建戏楼或关公诞辰于庙楼演戏一样,既可娱神又可娱人。如此,这三组朝向一致而且先建的房址(F9、F17、F18)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也增添了F17为家庙的可能性。
土司于衙署内建家庙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永登鲁土司祖先堂设于衙署中轴线后端,忻城莫土司祠堂设于右路,大屯土司庄园余氏宗祠设于左路,武定慕连土司祖宗堂在中轴线末端,其前为左右两厢,分别为用人房与祭祀用厨房。而这种现象则断不可出现于府州县等流官衙署中,在于流官有任期而土司世守其土。文献记载显示其家即其衙,家衙一体,这也构成了土司衙署的一个鲜明特点。
如果说中轴线上的治事之所是土司政治权威的表达,那么凸显宗法意识的家庙则是土司合法性的血缘依据。按制,土司袭替朝廷有明确的规定,如拟袭者需提供“宗支图本”,有“官吏人等结状”,经官员“体勘”后方能上报,同时“土官册报应袭法”即预定承袭人[25]。《勘处播州事情疏》记载了一个职衔较低的长官司长官袭替的案例:“成化三年(1467)八月内,本司长官何庸病故户绝,有伊族侄何熙庆不合捏称系何庸嫡长男,告袭前职。杨辉不合准信,拘集亲族里老审取结状,备申四川都布按三司覆勘,具奏准令,冒袭前职。”[26]冒充亡故长官的嫡长子,相当于提供“宗支图本”与土官应袭法;而袭职须有“结状”,其上司宣慰使杨爱通过“拘集亲族里老审取结状”得以实现;而后报“四川都布按三司覆勘”,并获通过。杨氏有“宗支图本”,自杨粲开始重塑祖源记忆,至明初宋濂撰《杨氏家传》,为其提供了清晰的宗支叙事。同时“杨氏家法,立嗣以嫡”[27],即其“应袭法”。该“家法”至迟在杨文主播时即已订立,《杨文神道碑》记“君领郡,式遵家法”。继承土司职位的嫡长子遂成朱子《家礼》所规定的世守祠堂的“宗子”,负责主持家庙内祖先的祭祀。在此意义上,家庙是土司承袭合法性的血缘证据,因此在土司衙署中得以彰显。
土司通过始祖追认与祖先祭祀强化其内部认同,通过中央政权所赋予的职衔强化其政治权威,表现在衙署的格局上就是对两种礼仪性建筑的彰显:一是中轴线上的政治性礼仪建筑,与朝廷的要求保持一致,反映了土司的国家认同;二是宗族性礼仪建筑,将家庙置于衙署十分显著的位置上,强化宗法意识而实现家衙一体的衙署布局。两组建筑,遂成土司合法性的政治与血缘表达。由此,便可理解为何土司普遍将家庙建于衙署之内,而“新王宫”内F17应即杨氏家庙。
四、结语
结合建筑格局、其他衙署资料与文献记载,可知“新王宫”为明代海龙囤的内城,其性质为土司衙署。现存主体建筑由杨氏第30世土司杨应龙创建于明万历时期,最终毁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播州之役战火。明代建筑在营建顺序上存在先左后右、自后而前的趋势,但“新王宫”系整体规划、一次建成的。从地形推断,“新王宫”可能也是南宋“龙岩新城”的衙署所在地,但目前发现的零星南宋遗存尚不足以对此做出肯定回答。明代衙署毁弃后,海潮寺僧众成为“新王宫”的主人,也留下了不少遗迹、遗物,但已与土司无涉。“新王宫”明代土司衙署整体格局呈三进三路,有治事之所、宴息娱乐之所与仪礼宣教之所。自前而后中路依次为大门(F28)、仪门(F25)、六房(F23、F24)、大堂(F22)、两厢(穿堂)、二堂(F7)与土司卧房(F8);左路为吏舍(F26)、土司家眷居所(F2~F4、F30)、总管厅(F19)、宴会厅(F20)、神厨(F9)、戏楼(F18)与家庙(F17);右路为客舍(F29)、吏舍(F27)、监房(F13、F14)、府库(F10)、马厩与用人房(F11)以及宴游之所(F1、F12与C1)。呈现前衙后邸、左尊右卑的布局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粮食作物在各房址的普遍出土,反映在播州之役爆发的特殊情况下,多数房址可能曾被挪作粮仓之用,以保障供给;同时随囤上驻扎人员的激增,原先规划的建筑功用可能被临时调整而辟作他用。
注释:
[1](明)申时行重修,(民国)王云五总编纂:《明会典》卷六二《礼部二十·房屋器用等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79、1580页。
[2](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3](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七《破囤塘报》,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57页。类似记载亦见于(明)栖真斋名衢逸狂演义:《征播奏捷传》第四十二回:杨应龙见大势已去,“乃令军士开各库藏,取出金银珍宝,罗缎细帛等物,分散众将”,遵义县文化体育局、遵义县文物管理所点校本,2004年,第186页。
[4]王贵祥等著:《中国古代建筑基址规模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07~109页。
[5](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五《叙功疏》,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6](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四《献俘疏》、卷五《叙功疏》,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25~126、150页。
[7]李飞:《宴会、戏台与影堂:墓葬中的生死》,《当代贵州》2017年第46期。
[8](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10、64、74、90页。
[9](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65页。
[10](清)顾彩著,高润身等注释:《容美纪游注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7、45、59、78页。
[11](宋)朱熹:《家礼》卷一《通礼》,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75、876页。
[12](正德)《明会典》卷八八《礼部四十七·祭祀九》“品官家庙”与“祠堂制度”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24页。
[13](宋)朱熹:《家礼》卷一《通礼》,第917页。李飞:《夷夏之间:播州杨氏羁縻·土司墓葬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27~129页。
[14]《忠烈庙碑》载(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一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2页。
《杨粲墓志铭》参见谭用中:《杨粲墓及其出土碑志考》,《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杨氏墓志铭文参见李飞:《夷夏之间:播州杨氏羁縻·土司墓葬研究》附录一“播州杨氏出土与传世文献选录”,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348~350页。
[15]关于杨氏的祖源,出土的《杨粲墓志铭》因残缺不全,未见杨端自太原入播的明确信息,但有“蜀无壅塞之患,而六诏绝烽烟之警,求其……秦潞二王为节度使。思权死,弟思勉得旨出家”的零星记载。其中,“秦潞二王”,为唐明宗之子李从珂(潞王,曾为凤翔节度使)、从荣(秦王,曾为河东节度使);“思权”即杨思权(875~943),邠州新平(今陕西彬县)人,先后事秦潞二王,曾任“邠宁节度使”。此杨与播州杨氏的关联不明。至《杨文神道碑》(当撰于杨文下葬的1267年前后)则称“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其功始著。五季乱,天日离隔,杨氏世守其土”。首次叙及杨端入播,但未言明祖籍何地。元大德六年(1303)《杨文神道碑》记:“杨氏系本太原,唐乾符初赠太师讳端者,宦游会稽,后客长安。适南诏 播州,大为边患。有旨募能安疆场者,太师慨然自效,遂命为将,以复播州。威畅恩融,夷夏畏服。因领其郡,是为播州杨氏始祖。”第一次明确杨端祖上为太原人,杨端自己则先宦游会稽,后客居长安,再领兵入播,而成播州杨氏始祖,这成为后世祖源叙事的范本。(《杨文神道碑》志文参见李飞:《家事与国事:关于贵州遵义出土〈杨文神道碑〉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此后元人袁桷(1266~1327)所撰《杨汉英神道碑》称“乾符鼎移,五季嗣兴。维并杨氏,太师肇初。往理其疆,以黜以助”,延续了《杨文神道碑》杨端乾符入播的叙事﹝载(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8~351页﹞。元至正六年(1346)《玉皇观碑》记“播自唐乾符间,太师杨端肇基此土”。明初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六五《杨赛因不花传》记杨汉英(杨赛因不花)“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诏陷播州。有杨端者,以应募起,竟复播州,遂使领之”。杨氏祖源写入官方正史,遂成定论。宋濂还专为杨氏撰写的《杨氏家传》称:“杨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旺族。后寓家京兆。唐末,南诏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诏募骁勇士将兵讨之。”与《杨文神道碑》的记载无甚出入。至明万历时,杨氏因此华夏身份而拒绝与水西安氏(彝族)通婚,《平播全书》卷十四《书札·杨监军》记:“安曾求亲,杨氏不从,求以女嫁之,亦不从。盖自负为太原诗礼旧家,而安为猡鬼,耻与之同盟也。”足见祖源记忆对土司的影响。第13世杨粲既“封太师公为始祖”,虽其墓志铭因文字缺损而叙事不清,但可肯定杨氏祖源叙事的范本此时已定,杨氏后人与时人不过延续其说而已。杨氏为土著之说,参见谭其骧《播州杨保考》,原文发表于《史地杂志》第1卷第4期,1941年;加后记再刊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16]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
[17]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第77~94页。
[18]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19](清)郑珍、莫友芝编纂:《遵义府志》卷二《建置》、卷三一《土官》,巴蜀书社,2013年,第30、603~610页。
[20]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5~57页。
[21](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94页。
[22]孙伟杰:《“籍系星宿,命在天曹”:道教星辰司命信仰研究》,《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2卷第1期。
[2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志第一·天文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93页。
[24](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79页。
[25]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5~146页。
[26](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
[27](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
本文原刊于《西南文物考古》第一辑
文稿:李飞









 重庆考古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