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800年的英雄城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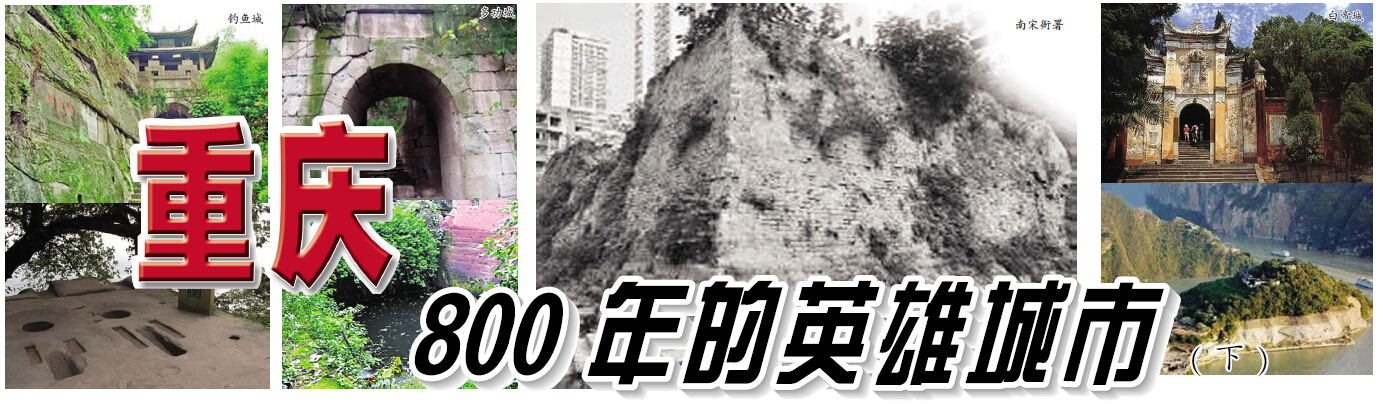
2014年5月14日,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部分委员,第三次前往南宋衙署遗址调研。每一次调研的委员和时间都不相同,但张罗人都是林必忠。
林必忠有着双重身份,他既是一位资深考古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又是位资深政协人,自2003年于今,已蝉联三届重庆市政协委员,其中一届担任常委,上一届和本届,他还是学习及文史委副主任。
34年前,林必忠师从童恩正(《古峡迷雾》、《珊瑚岛上的死光》作者)教授,从恩师教导他那一刻起,考古事业成了他一生的追求。十几年作政协人,让他为重庆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到了殚精竭虑。他借自己的名字笑说:“我必须忠诚文物事业”。
他是一名民革党员,他所在民主党派组织领导——原民革重庆市委主委、全国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夏培度,曾送他一个称号,叫做“热血党员”。“热血党员”于林必忠讲,绝无虚名。十几次的政协全会上,他3次向市委书记、市长当面直谏,数十次提案(被媒体誉为提案大王)、社情民意,都是为了文物保护而为。因为参政议政成绩卓著,林必忠连续两届获“重庆市政协优秀委员”称号;又因为保护文物成果昭然,受社会公 众推荐,以“执着坚定的文物守护人,斗智斗勇的考古界战士”为上榜理由,获2007年“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奖。
算上做政协人之前的时间,二十几年中,保护文物与城市建设的激烈冲突,传统文化与经济建设价值观的猛烈碰撞,让他很有些疲惫不堪,其中的艰难与艰辛,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幸运的是,近十几年里,他成为一名政协委员,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虽然有句话叫“政协就是两味药——甘草和白芍”,然而,无论得罪政府部门也好,还是得罪建设业主单位也罢,他仍然一直坚守“必须忠诚文物事业”这一信念。在他十几年的参政路上、十几年的疾呼声中,北碚老舍旧居(《四世同堂》在此写作)、江北城清代城墙、城门,渝怀铁路重庆段文物等等,都有幸得到保护。他还直接推动了三峡水利枢纽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再就是有个阶段性成果,那就 是《重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的出台,和他的呼吁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这处距今770余年的宋代建筑遗址,何以说它是重庆等级最高、价值最大的古建筑遗址?”委员们的疑惑,在袁东山的讲解下,得以透彻。
遗址在地面上能见到的,是一个小山包,夯土包砖式建筑基址全由青砖砌成。袁东山指着一块厚厚的青砖上模糊的字,让委员们辨认。原来,青砖上面有“淳祐乙巳”铭文字样。袁东山说:“‘淳祐乙巳’即1245年,正是属于南宋末年余玠主持抗蒙战争时期。”
资料记载:余玠,南宋末期名将。宋理宗时,因见四川战局不利,任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命于四川危亡之际,表示“愿假(借)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余抵重庆后,广纳贤才,修筑工事,恢复经济,安抚民心,统率十万军民到合州(今合川)修筑钓鱼山城;又在三江(长江、嘉陵江、涪江)沿岸山险处筑数十城。各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屯兵聚粮,形成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入蜀当年,便在资州、嘉定、沪州等地,赢得了与蒙古军大小36战的初步胜利。1246年春,蒙古军大将塔塔歹贴赤分兵四路入侵四川,余玠率军抗战。以新筑之山城为屏障,重创蒙古军。1252年10月,蒙古军汪德臣、火鲁赤部大规模入侵,进抵嘉定,余调集蜀中精锐部队,组织大规模会战,将蒙古军击退。余玠因抗蒙治蜀有功,于1252年晋升为兵部尚书。
从余玠介绍中可以看出,四川安抚制置府治所就在重庆。早在袁东山们介入之前,为了拿到确凿的证据,渝中区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把墙砖带回所里鉴定,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小山包周边区域,就是一座城池,就是之前考古人员苦苦寻找的南宋重庆城!
袁东山说,从史料记载可以推算,这个地方,当年宋光宗赵惇在此做恭州王时,驻扎就在此处,办公居家两用。到余玠主政时,这里又是他的帅府所在。余玠在重庆设招贤馆,广开言路,馆址亦应在此处。
余玠为何叫帅?原来,在宋理宗时期,南宋的版图已缩得很小,北方大部已被蒙古占据。全国分为三大战区,每个战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统筹管理。三大战区之一的四川制置司,管辖着今天的陕西南部、云南、贵州东部和川渝地区。四川制置司办公机构(衙署)设在重庆,即如今发现的南宋衙署遗址上。
从现场步行几分钟,就到了金碧山脚下——渝中区文管所那栋有些年代的老楼房。在这里,袁东山向委员们展示了他复原的衙署结构图。他讲解说:“重庆市渝中区南宋衙署遗址的构造,完全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的规制,但又有着其鲜明的巴渝地域特色。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地处金碧山下、长江左岸的台地之上,背山面江、坐北朝南。
“遗址兴建于宋蒙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著名的川渝山城防御体系即在此筹建经营。”
川渝山城防御体系,即余玠主政时所建:从嘉陵江、涪江到长江,沿江依崖共建起数十座山城,它们分别是合川钓鱼城,渝北多功城,重庆母城(南宋衙署大本营,川渝山城防御体系指挥中心),南川龙崖城,万州天子城,忠县皇华城,云阳磐石城,奉节白帝城等等。

“作为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重庆渝中区南宋衙署遗址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作为四川制置司衙署所在,衙署遗址具有厚重的文化遗产价值;作为重庆城市考古的关键填空,衙署遗址是重庆城市发展史的实物见证、人文精神的珍贵载体,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作为南宋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枢纽和指挥核心,它又是一处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军事遗产。”
“南宋衙署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重庆城市沿革变迁、川渝地区古代建筑及宋蒙战争史有重要学术价值,对保存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打造城市名片、彰显‘英雄之城’形象,以及提升重庆文化品位,具有突出的文化遗产价值和展示利用价值。”
“它还极具艺术价值:南宋衙署遗址规模宏大、布局清晰,作为遗址标志的高台建筑遗址的断壁残垣,矗立于现代都市核心圈内,在巨大的反差下,营造出一种沧桑、悠远的艺术审美氛围。现存的大型砖砌墙体、巴县衙门衙神祠等建筑形制复杂,局部雕刻精美,具有鲜明的西南地区木构建筑特点。”
自打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那鼓舞人心、提神提气的南宋衙署遗址保护利用蓝图后,袁东山每每沉浸在上述构思和向往中,每每在保护和利用报告中,描述的都是一幅幅提升重庆历史文化底蕴的画面。然而,2012年9月24日,在重庆市政府第134次常务会上讨论通过的《南宋衙署遗址保护利用与教育建设概念规划研究》,敲定了南宋衙署遗址保护方案,决定将南宋衙署遗址与文化街中学复合建设。
复合建设有具体阐述:“西部为文化街中学建设与文物保护复合用地……为保护明清院落遗址,对遗址西部核心区域进行可逆性保护,回填作为学校操场及室外环境,教学楼沿文化街及解放东路呈“L”型布置,新建建筑基底不占用重要遗址,学校建筑外观设计为传统建筑风格,并与南宋衙署遗址公园整体风貌相协调。”
当袁东山被告知这一“保护利用”决定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字在吼:“不!”但他又被另一个消息勾起希望,因为黄奇帆市长当时有一个批复:“要将南宋衙署遗址这一文化遗产珍品,建成渝中半岛高楼群体中彰显历史文化底蕴的丰碑。”自那个时候起,他多次将新发掘出的、愈发珍贵的文物报告,送达主管部门,但“保护决定”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他对本报记者说:复合用地,可逆性保护,就是一个意思:遗址得不到完全保护!他向记者解释“可逆性保护”:“用回填土把文物埋葬了,在上面修建筑,以后需要了,又把它翻出来。”他言辞有些激动:“难道见证800年的英雄城市历史的遗址,还不足以抵档一个学校么?”
其实,在遗址现场,委员们也是这个意思。他们说,渝中区的学校可以置换到更适合的地方,而老祖先的遗产,却无法再生。孰轻孰重,不是一目了然么!袁东山一针见血直逼要害:“就是那块土地值3个亿的问题!”委员们则认为,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是有无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观念问题。
说到钱,本报记者想起今年7月,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到福州市考察历史文化保护。福建省政协文史委的同行听说重庆南宋衙署保护困难时,便给我们讲了一个广州大力度保护文物的真事:
1995 年,在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及北京路交叉口的东北角,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及相关建筑,遗址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是,广州市政府在市中心区——广州建城以来的政治中枢所在、寸土寸金的繁华商业地段,果断停建、改建了多项建设工程,花费巨资(3个亿乘20都不止)搬迁有百年历史的儿童公园,以扩大遗址的发掘,为切实保护南越国宫署遗址奠定了基础。2009年8 月,南越王宫博物馆正式开工。南越王宫博物馆以保护、展示遗址和服务考古为主,以出土文物陈列展示为辅,并实现教育宣传、文化休闲等功能。
是否可以借鉴他山之石?!
本文发稿之前,记者再次联系林必忠,他说,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看到习总书记讲话:“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他认为,此讲话精神,同理可用于传统文化保护。然而,重庆开这个会时,他这个文物考古研究员、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副主任又没有资格参加,想说都没地方说。
南宋置司、抗战陪都、中央直辖,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三次大飞跃,而南宋置司是重庆城市大发展之发端。南宋衙署遗址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高台建筑遗迹直接树起了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作为重庆人,我们应该保护好它,让它永远为重庆城市发展作证!为800年的英雄城市作证!
(完)
(重庆政协报 总第2154期 2014年12月19日 第4版)
本报记者 郝成竹









 重庆考古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