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考古学萌芽至诞生以来,不乏女性学者在这片领域内彰显巾帼风采,她们量少而弥珍,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贡献丝毫不逊于须眉。作为国内考古文博领域的开拓者和建设者,她们抒写了中国考古学史浓墨重彩的一笔,是绽放在青史册页间的铿锵玫瑰。
一、近代中国金石考古的先声 ——容媛

图1 容媛与容七娪
(图源:广州数字图书馆)
1899年12月,容媛先生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市莞城镇中的一个书宦世家,序齿行八。家中四舅父是当世书法篆刻名家邓尔雅先生,两兄长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另一位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家容肇祖先生。容媛先生少时曾受舅父开蒙,后师从长兄容庚,并在其影响下,终生致力于金石目录学研究,为近代金石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容媛先生因家学底蕴深厚,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少时,面对女性地位极其低下的社会现实,先生痛心而愤怒,后与家中姊妹共同创建妇女工读学校,从此积极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先生本人曾考入由何香凝、邓颖超等杰出女性组织任教的中央妇女部学校学习,其后又在中山大学旁听。1931年,容媛先生进入燕京大学担任学报编辑,“国内学术界消息”专栏由此产生。
“国内学术界消息”专栏涉及考古、历史、文学等社会人文科学各方面内容,除了对前沿学术成果的介绍外,其中往往还融入了容媛先生自己的独到见解。该专栏不但是当时学术信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媒介,极大程度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学科史料,是研究学科发展脉络的珍贵素材。
容媛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生前曾有《经籍要目问答》和《金石书录目》两部要作面世。其中,《经籍要目问答》目前仅见民国刊复印本。另一巨作《金石书录目》由容媛先生编著、先生之兄容庚先生校对,1930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次排版发行。初版铅印本收录书目822部、方志金石志190部、金石丛书12部。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时作了增订,新增书目122部、方志金石志107部。至1955年《金石书录目补编》发表,全书共收录书目1215部、方志金石志297部、金石丛书12部,其涵盖之全面、分类之严谨,在当时前所未见。直到今天,《金石书录目》依旧是考古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参考书目。
此外,容媛先生尚有不少研究,因历史原因被迫中止,没能最终完成。
其一,是先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辑录的秦汉石刻题跋,文革时期不知所踪。垂垂暮年时,先生仍因遍寻不见这些石刻资料而愤懑不已。直到本世纪初,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学专家胡海帆先生受高明先生所托,《秦汉石刻题跋辑录》[1]方才承袭容媛先生遗志得以重新整理出版。该书收录了历代学者对359种秦汉石刻的题跋,内容涉及自宋代至民国中期以前的历代金石书籍、方志和文集中有关秦汉石刻及其拓本的著录、研究、考据和论述。《秦汉石刻题跋辑录》的成书材料在容媛先生手中已具规模,却跨越了近一个世纪,才得以面见世人。
其二,是先生于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搜集整理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86年夏天,贾梅仙先生接手了这些文献卡片资料的重新整理工作。贾先生后来在《容媛传略》中道:“近来考古系资料室对此目录又重新进行了加工整理和补充,已经定稿,准备付梓。如果该书能出版面世,则又为我国考古学界提供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2]1991年,《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3]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适时,容媛先生尚在人世,晚年夙愿达成,不知先生心中可否稍感慰藉。
1996年1月,容媛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7岁。终其一生,先生不曾婚嫁,无有后嗣。她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枯燥繁复的金石考古辑录工作,为金石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近代中国考古学的蓬勃生机力作先声。
二、金石文字考古的引路人 ——游寿

图2 晚年的游寿先生
(图源:王立民.文心雕虫[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3.06,第85页.)
1906年农历九月,游寿先生出生于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先生祖上世代书香,高祖游光绎工诗善书,去官后回到家乡,在当时福建的最高学府“鳌峰书院”掌教近二十年,民族英雄林则徐即出自其门下;曾祖游大琛与林则徐有同窗之谊,道光年间中进士;祖父游宝荣长于书法,但不幸早亡;父亲游学诚年少持家,十五岁从教,后主持“近圣书院”(今霞浦一中),又在家乡首创女子高等小学,在当时是有名的教育家,更是难得的女权支持者。在这样的家学背景下,游寿先生作为家中独女,自小不曾受到穿耳裹足等针对女性的封建迫害,开明有爱的成长环境造就了先生聪颖独立的脾性,也为她日后的治学之路奠定了基础。
1920年,游寿先生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师从邓仪中先生,接受书法启蒙;1928年,又赴南京,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跟随胡小石先生研究金石书法和先秦文献。胡小石先生的书法承自李瑞清先生,所以游寿先生也深受李瑞清先生“学书必须习篆,不善篆则如学古文不同经学”这一主张的影响,于书法一道始终践行“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的理念。“化碑入帖”的行文办法要求学书者深钻金石碑铭,这也为游寿先生开启了金石研究的门径。
游寿先生的作品以诗文书法居多,如《伐绿萼梅赋》《山茶花赋》《山居志序》《沙溪集》《饥妇行》等,皆是传世大作。姜勇先生对游寿先生的书法曾作“格度超迈雄恣,不让男性书家”的评价,并认为,这或许“与20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有关”[4]。但先生的功绩绝不止书法一项,她并非只是端坐静室舞文弄墨的文人,她还是一位真正的金石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
1960年,游寿先生在哈尔滨东郊考古,在出土的猛犸象骨骼上发现了人工凿击的痕迹,由此判断黑龙江地区在石器时代曾有古人类生存活动。随后在沙曼屯、万家等地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又进一步验证了先生的论断。1980年,游寿先生基于上述考古活动,与于莲英先生合作发表了《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呼盟的旧石器晚期骨制工具》[5]一文。
1979年,游寿先生根据魏碑墓志,推断《魏书》中记载的北魏石室祖庙应在嫩江流域。在游寿先生的启发下,次年,米文平先生三上大兴安岭考察,终于找到了拓跋鲜卑民族的神秘发祥地——大鲜卑山嘎仙洞。山洞石壁上201字魏书祝文的发现,被列为新中国重大考古成果之一,载入《中国历史学年鉴》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游寿先生的弟子王立民先生在《游寿传略稿》中这样评价道:“如果没有游寿先生在黑龙江考古学术讨论会上对米文平有关‘石室’的提示,这项发现也许会向后推移几十年、几百年,或许永远不能成为现实。”[6]
1981年春节期间,游寿先生返乡探亲,全然不顾自己已年逾古稀,执意前往福建沿海的赤岸村考古调查。经走访,先生确认赤岸村即是唐代中日往来的海港重镇赤岸镇,并找到了大量唐宋时期的遗物遗迹,证实这里就是日本遣唐使登陆华夏大地的重要口岸之一。
1934年,游寿先生与陈幻云结婚。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段婚姻早年并不为人所知,以至于先生在四川南溪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时,因长期前往重庆与丈夫团聚,被不明就里的傅斯年忿然停职,连期间完成的《冢墓遗文史事丛考》也被拒绝付印。[7]在李庄与傅先生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是游寿先生最不愿提起的回忆,但却恰恰是受此影响,五十年代,先生被划入傅斯年学阀集团,接受思想改造。文革期间,先生又被扣上了“历史系八大怪”的帽子。此时,先生之夫已逝,幼时侥幸躲过封建残害的她,这一次却终于没能逃开批斗和抄家的命运,独自一人经受了这场时代洪流的碾压和蹂躏。直到1972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当时国内能够识得甲骨文的学者不出十人,其中就包括游寿先生,先生这才在周总理的关心下从边远山区被调回哈尔滨师范大学。先生浮萍一生,终于安定。
1994年2月16日,游寿先生溘然离世。先生的一生是真正的“游者”,自1920年首次离家求学,先生天南地北东西辗转,足迹踏过9个省份,到晚年才终于定居哈尔滨。当时的书法界有“南萧北游”之说,“南萧”是指南社社员萧娴先生,而“北游”说的便是身在东北的游寿先生。可先生毕生不曾改变福建口音,却是个地道的南方人。她秉承家风,终身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一生曾辗转厦门集美师范、济南女子师范、南京汇文女中、福建省立一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哈尔滨师范学院等国内多所院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虽有桃李布天下,自己却半世孤独,四海为家。
游寿先生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教育家之一,同时也是杰出的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她潜心钻研,培养了大批金石文字与考古事业的继承者,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引了一条生生不息的道路。
三、 中国考古学无法越过的开章 ——曾昭燏
1909年2月3日(一说1909年1月27日,此处采信南京博物院于1999年[8]和2009年[9]两次编辑出版的《曾昭燏文集》中的说法),曾昭燏先生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荷叶镇硖石村“万宜堂”,家中兄妹七人,先生行三,是家中长女。先生的曾祖父是晚清名臣曾国藩之弟曾国潢,先生幼承庭训,能诗善词。五岁入家塾念书,接受传统旧式教育,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十四岁入堂姐曾宝荪创立的艺芳女校,接受时新的西式教育。受堂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先生不愿为家务牵累,年少时便立志不婚,愿以有限的精力去服务更多人。

图3 曾昭燏先生
(图源: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8.)
1929年,曾昭燏先生考进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与游寿先生一前一后拜入胡小石先生门下。1935年,曾昭燏先生在兄长——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曾昭抡的支持和资助下,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硕士学位,成为我国最早留学国外的考古学人之一。留学期间,先生结合在德国的实习经验,完成了《博物馆》一书草稿。1943年7月,《博物馆》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李济先生增名合著。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释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的专著,是西方博物馆学理论与我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对现代博物馆和博物馆职能作出了规范性的定义和阐释,是我国博物馆学产生与发展的奠基之作,其意义与影响不言而喻。
1938年,曾昭燏先生放弃伦敦大学的助教工作,毅然回国投入全民抗战。先生早年致力田野考古,曾在云南大理、洱海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又因战争局势将工作重心转移至四川,在彭山江口一带开展考古发掘工作。1942年,先生与吴金鼎、王介忱等合作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由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筹备处付刊出版,开启了云南地区现代考古研究的发端,为日后该地区的古史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曾昭燏先生随中央博物院迁返南京,参与清点战时文物损失。先生非常重视文物的征集与保护,曾竭力保护国宝,坚决反对将文物运往台湾,并发出声明:“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10]在她与吴有训等众多爱国学者的努力下,台湾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抵台的852箱珍贵文物归还大陆,但仍有旧藏于中央博物院的647件书画从此转藏台湾。为此,先生与众专家学者协同开展文物征集与鉴定工作,其后陆续为博物院新征古代书画珍品三万八千余件,极大程度提升了博物院书画藏品的数量与质量。
1950年9月,中央博物院正式更名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先生出任博物院副院长,1955年升任院长,次年评为正高级职称。在积极投入新中国文博事业建设的同时,曾昭燏先生仍没有放下田野考古,百忙中依旧亲自主持了南唐二陵和山东沂南画像石墓这两项重大考古发掘任务,并参与编写了考古发掘报告。
不同于国内部分考古学者重田野发掘、轻室内研究的偏见,在曾昭燏先生看来,“那些付出了巨大的创造力劳动的博物馆工作,它们的价值是绝不比搜集到资料,编写出报告或论文的价值弱些的。”[11]在博物院管理工作中,大到展陈设计、文物管理,小至展品的文字说明,先生一贯亲力亲为,要求严格而精细。罗宗真先生曾在文中回忆道:“曾院长对新同志有一条纪律,这是一条不成文的院规:凡是搞文物工作的干部,尤其是做考古工作的,绝不准私人收藏文物,永远不玩古董。”[12]这样的规矩被“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确令为考古文博行业的“三不主义”——即考古人不收藏古物、考古人不买卖古物、考古人不鉴定古物——至今仍被学界业界严格遵奉。
先生晚年因重度抑郁精神不佳而难以入眠,1964年3月9日起入南京丁山疗养院住院治疗。或许是恩师胡小石的去世带来的打击与悲恸,更可能是因为包括兄长曾昭抡在内的尊亲师友被打为“右派”并遭遇不公迫害而招致的惶惑与愤怒,当年12月22日,先生留下仅有日期、空白无字的最后一篇日记[13],从南京灵谷寺宝塔上跃下,匆匆结束了自己仅55岁的生命。
曾昭燏先生是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唯一录有独立词条的中国女性考古学家[14],她将自己的一生“嫁给”了考古与文博事业,“嫁给”了南京博物院。那个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界有“南曾北夏”一说,指赞曾昭燏先生与夏鼐先生这两位比肩齐名的国内顶尖考古学者。曾昭燏先生的猝然辞世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无疑是无以弥补的缺憾,但就先生的家庭出身来看,免于经受往后十年那场席卷全国、更加疯狂的风暴,于先生而言又或许未必不是一件幸事。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奠基人之一,曾昭燏先生是后世中国考古学史研究中无法越过的巨匠,她为考古事业和文博建设作出的贡献,应该被中国考古学永远铭记,奉为开章。
四、美术考古之母 ——何正璜

图2.6 王子云、何正璜夫妇
(图源: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何正璜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6.)
1914年6月1日,何正璜先生出生在日本东京的一间租屋内,日语乳名译作“玉子”。但先生并非是日裔外籍——先生籍贯湖北汉川,祖籍是江西南昌三花桥村;母亲张佳牗(后改名张楚)亦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先生幼时家道殷实,祖上世代读书做官。祖父何宗瀚早年携子(先生之父何竞择,又名何立夫)留洋日本,归国后倡导改革,投身司法,曾在多地担任检察厅或审判厅厅长。在祖父的启蒙下,何正璜先生幼时便博览群书,养成了耐心沉稳的品性,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小学就读于湖北省女师附小,初、高中就读于湖北省女子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进入武昌美术专科学校,1934年赴日本东京多摩川高等美术学校留学——因父辈提倡女子同男子一样读书学习,故先生得以在当时那个年代接受到如此系统完整的教育。1937年,惊闻“七七事变”,先生毅然中止学业,迎着战火愤然回国。虽则先生在日本时并非专修考古学专业,但就其日后经历来看,先生应与曾昭燏先生同是那个年代最早留洋归来的女性考古学人。
1940年8月,苦于报国无门的何正璜先生偶然从拾得的报纸上看到一则“征聘建筑绘画人才”的消息,冥冥中她感应到这则消息的背后另有文章,于是离开湖北,只身前往重庆。是年,先生应聘进入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结识了年长自己17岁的考察团团长王子云,并成为王子云先生“家乡外的妻子”[15]。1940年12月27日,考察团结束在四川为期三周的集训,由成都启程前往陕西,正式开始西北考察之行。
此后直到1945年考察团解散的5年时间里,何正璜先生跟随丈夫带领着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足迹踏遍川、陕、豫、青、甘五省,“为敦煌艺术研究做出开创性的贡献”[16]。何正璜先生作为考察团里唯一的女性,既要随团走访、速写绘画、记录和整理考察团的工作日常,又要负责照顾身为考察团团长的丈夫的饮食起居,其中辛苦,更甚一般队员。但出于对祖国文化艺术的热爱,在考察期间,先生百忙中仍坚持记录日记。在日记中,先生写道:“本团在现代中国所负之使命,如古代文化艺术之正式统计、调查、描绘、模塑、分类、保存等,允为中国艺术界之开荒工作……故我们不量才力,不畏风霜,不避艰辛而作此劳苦工作,乃国民之本分,更为艺人之光荣也。”[17]这些文字后经王蔷、任之恭、崔文川等先生的整理,辑成《西北考察日记》出版,成为了解和研究这次西北考察工作最为直观的一手材料。
在敦煌期间,何正璜先生共临摹了至少15幅壁画,并于1943年发表《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18]。这是国内首次见刊的关于莫高窟的全面调查报告,《中国敦煌学史》中评价道:“当时到敦煌实地考察千佛洞,利用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成绩显著者,首推何正璜。他(她)在《说文月刊》第三卷十期上发表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是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何正璜此文作为中国学者实地考察研究敦煌石窟后写成的第一篇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文章,其历史价值是很重要的。……第一,此文第一次把敦煌石窟立体地介绍出来。……第二,在敦煌艺术的风格研究上,作者首次提出敦煌早期艺术之作风倾向:‘系以东方装饰之趣味,混以西方写实之技巧,而另成一种风格。’‘其内容与形式均足以代表东西交流之特征。’……较之‘西来说’无疑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19]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最初成团的缘由,是为了提防西北后方的文物遭日军破坏或盗走,故需提前前往实地考察,以尽可能为后世研究留下真实详尽的图文资料。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没有了存续的理由,加之国民政府经费难以维持,考察团只得解散。随后,王子云先生应邀赴西北大学挂名为教授,并在何正璜先生的协助下建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西北大学博物馆前身),由何正璜先生担任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1953年,何正璜先生被安排进入西北历史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在这里,先生如鱼得水,组织完成了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并一手创建起“西安石刻艺术室”。新中国的文博事业百废待兴,先生不但于碑林博物馆的展陈布置与讲解宣传上处处身体力行,更在接待周恩来总理时,一力促成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建成。为此,蔡昌林先生评价她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20]。
1994年10月22日,何正璜先生在经历了三场大手术后香消玉殒。先生去世后,人们在整理先生遗稿时发现了《唐陵考察日记》(现收录于《何正璜考古游记》)[21]。这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考古史上最为重要的文章之一。它第一次运用现代美术考古的方法,对关中唐代帝陵陵区内的文物信息作出了详实的记录,让人们看到了考古研究与报告行文的另一种可能性。
何正璜先生在文集自序中介绍自己“是一支蜡烛”,同时,也是搭建在美术与文博工作之间的一座桥梁,“这座桥是无形的,但却是有益的……行见美术界、文物界的两团智慧的光越靠越近,将会愈照愈亮,互相辉映,通过大桥,将是一片光明绚丽、万里锦绣的前程!”[22]
五、殷墟中的“女将军” ——郑振香
1929年10月,郑振香先生出生于河北省东光县。抗战胜利后,因家境并不富裕,为节省家庭开支,先生选择了报考位于天津的河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又于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1952年,在夏鼐先生的主张下,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博物馆专修科被取消,郑振香先生于是转入考古专业,进入了她当年“不敢考”的历史系[23]。1954年,先生本科毕业,服从分配留校担任助教。次年改作考古系研究生,师从张政烺、尹达、苏秉琦等考古大家,主攻商周考古。

图2.4 郑振香先生
(图源:郑振香.记忆殷墟妇好墓[J].大众考古,2014(04):19-23.)
1959年,先生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并于当年赴洛阳,任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队队长,参加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并辅导北大学生的田野考古实习。1960-1961年间,先生组织考古队共同编写出《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该书于1989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1962年5月,郑振香先生来到安阳殷墟,任安阳考古队副队长。此后直至2002年为照顾丈夫陈至达而离开考古发掘第一线,先生在殷墟停驻了整整四十年。来到这片考古圣地,为先生传奇的职业生涯拉开了序幕。
1976年5月16日,是个值得被载入中国考古史的重要日子。由于郑振香先生近乎执拗的坚持,在一片几乎要被考古队放弃的红色夯土之下,技工何振荣师傅费力地将探铲探入地下近7米深,终于在铲窝的泥土里发现了夹带着的红色漆皮以及一枚保存完好的玉坠。沉睡三千多年的古墓,在这一刻重见天日。
根据《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24]记载:妇好墓(M5)上建有享堂;墓葬中有殉人16具、殉狗6只;随葬器物共计1600余件(后更正为1928件),铜器440余件(后经确认,青铜器共计468件,其中210件为青铜礼器,铸有铭文者共190件,铭文铸有“妇好”或“好”者共109件,数量占出土青铜礼器半数以上),玉器590余件(实为750余件,含报告中说明不计入总数的百余件杂器),石器70余件,骨器560余件(其中绝大多数为骨笄),陶器7件;另出土海贝近7000枚(后更正为8600余枚,“均为货贝,经鉴定产于我国台湾、南海海域,另有阿拉伯纹绶贝、红螺等”[25])。1977年,妇好墓的发掘简报《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在郑振香先生和陈至达先生夫妇的主持下完成并发表。1980年,《殷墟妇好墓》[26]经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
对于将毕生精力投入殷墟考古的郑振香先生来说,妇好墓的发现与发掘或许是先生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然而先生于1962年提出的殷墟文化四期框架(这一观点被学界认同,并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所采纳),以及基于1989年安阳小屯村东大型建筑群的考古发现著述的《安阳小屯殷墟建筑遗存》[27],同样都是殷墟考古的重要研究成果。
妇好墓在考古学中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的唯一性和完整性——它是殷墟目前考古发掘中揭露的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墓葬,也是唯一一座可以与甲骨文记载对照考证,从而确定墓主人身份年代信息的王室墓葬。它的发现为殷墟的分期乃至“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参照依据。同时,它的完整性也为研究商代贵族礼制及其他重大社会问题提供了实物证据。在殷墟其他王室贵族墓葬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盗扰和破坏的情况下,妇好墓因深埋在厚厚的夯土层下而在历代盗墓者的手中幸免于难。但又正是这层坚沉厚重的夯土,让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与技工师傅们也险些误判。是郑振香先生对于学术的敏锐与坚持,叩开了这座在夏商周考古研究中地位举足轻重的千年古墓。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是这位四十年如一日埋首在安阳殷墟考古工地上的“女将军”,唤醒了另一位叱咤在千百年前的女将军,让战功赫赫的殷商王后妇好之名响彻新时代。这是跨越时空的奇妙缘分,更是足以名垂考古学史的伟大成绩!
六、田野里的荣光 ——郑笑梅
1931年2月,郑笑梅先生出生于浙江温州。1952年,先生进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张忠培、黄景略、高明、叶小燕等考古名家们成为同班同学。1956年,郑笑梅先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早年曾与叶小燕先生一同参加黄河水库考古队在庙底沟遗址和三里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后进入长江流域考古工作队,对丹江水库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1961年,先生调入山东省博物馆,从此扎根山东。

图2.5 郑笑梅先生
(图源:百度百科“郑笑梅”词条)
先生性格直率,在庙底沟时,因不满当时考古发掘与研究过程中对出土陶片拼对工作的不重视,与工地领队之间曾发生过龃龉。先生在60年代由考古研究所调往山东省博物馆,这次经历与其说是工作调动,不如说是天灾人祸的动荡时局下,有心人对先生的打压,于先生而言实为下放。对此,先生的大学同学、另一位杰出的女性考古学家叶小燕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她(郑笑梅先生)这人很能干,很努力,做事很有魄力,比较强的吧。在考古所受压没发挥大的作用,后来分配到山东以后,她就做出了显著的成绩。”[28]
1928年,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曾在龙山镇武原河畔的台地上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陶片,它们“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黑如漆”,厚度仅0.2毫米,故被命名为“蛋壳陶”。此后,“蛋壳陶”的残片虽然在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常有发现,但因胎体过于薄脆,很难有器形完整的“蛋壳陶”留存于世。直到1974年,郑笑梅先生主动请缨,对原山东考古所所长张学海先生在城子崖遗址发掘出的“蛋壳陶”碎片进行了仔细地研究比对,耗时半月,终于成功拼对出了一件完整的“蛋壳陶”器。
在山东,郑笑梅先生先初来乍到就接手了1960年姚官庄遗址发掘材料的整理工作。姚官庄遗址的发掘期正处在举国“大跃进”的高潮中,遗址的考古工作从发掘方式到发掘记录都深刻地烙印着时代背景造成的粗放和混乱的印记。1963年发表的《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发掘简报》[29],背后显然饱含了先生极大的心血与努力,同时也展示出先生的细致与耐心。此后先生又先后参与了野店遗址、大汶口遗址、东海峪遗址等多个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并整理出版了《邹县野店》[30]《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31]等重要考古发掘报告。
上世纪70年代开始,郑笑梅先生在山东大学开设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并指导研究生完成课题研究。1980年,在国家考古人才极度匮乏、真正从事田野考古的人员多非专业出身的前提下,国家文物局有意开设田野考古领队训练班,以填补考古实践中的人才空缺。1984年,第一期“田野考古工作领队培训班”在山东兖州开办,负责教学工作的是郑笑梅与苏秉琦、俞伟超、吴汝祚、张忠培、严文明、张学海、孔哲生、黄景略、叶学明等一众考古学领域的大家。田野考古培训班为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田野考古发掘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田野考古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对于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凡。而为后世中国田野考古培养出一众骨干力量的授业老师之中,便有郑笑梅先生这样一位外刚内柔、直率而又细致的女性考古学家。
2014年1月22日,郑笑梅先生病逝于山东济南。先生一生致力于田野考古,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中建树颇多。因与丈夫蒋英炬先生常年忙于田野工作,甚至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先生为中国考古事业奋斗在田野里的身影,足可以教今天的女性考古工作者们奉为榜样,共沐荣光!
七、“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
1938年7月9日,樊锦诗先生作为家中的第三个女儿,出生在战火沦陷的北平。先生之父樊际麟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工程师,从给两个孪生女儿起名“樊锦诗”和“樊锦书”,可以看出他对于女儿们饱读诗书的殷切期望。为避战乱,先生幼时起便举家搬迁至上海。先生祖籍杭州,又是在上海长大,按理说,她本是个地道的江南女子。谁知就是这样一位体娇病弱江南女子,却在命运的安排下扎根西北,从此一生“正定”,“守一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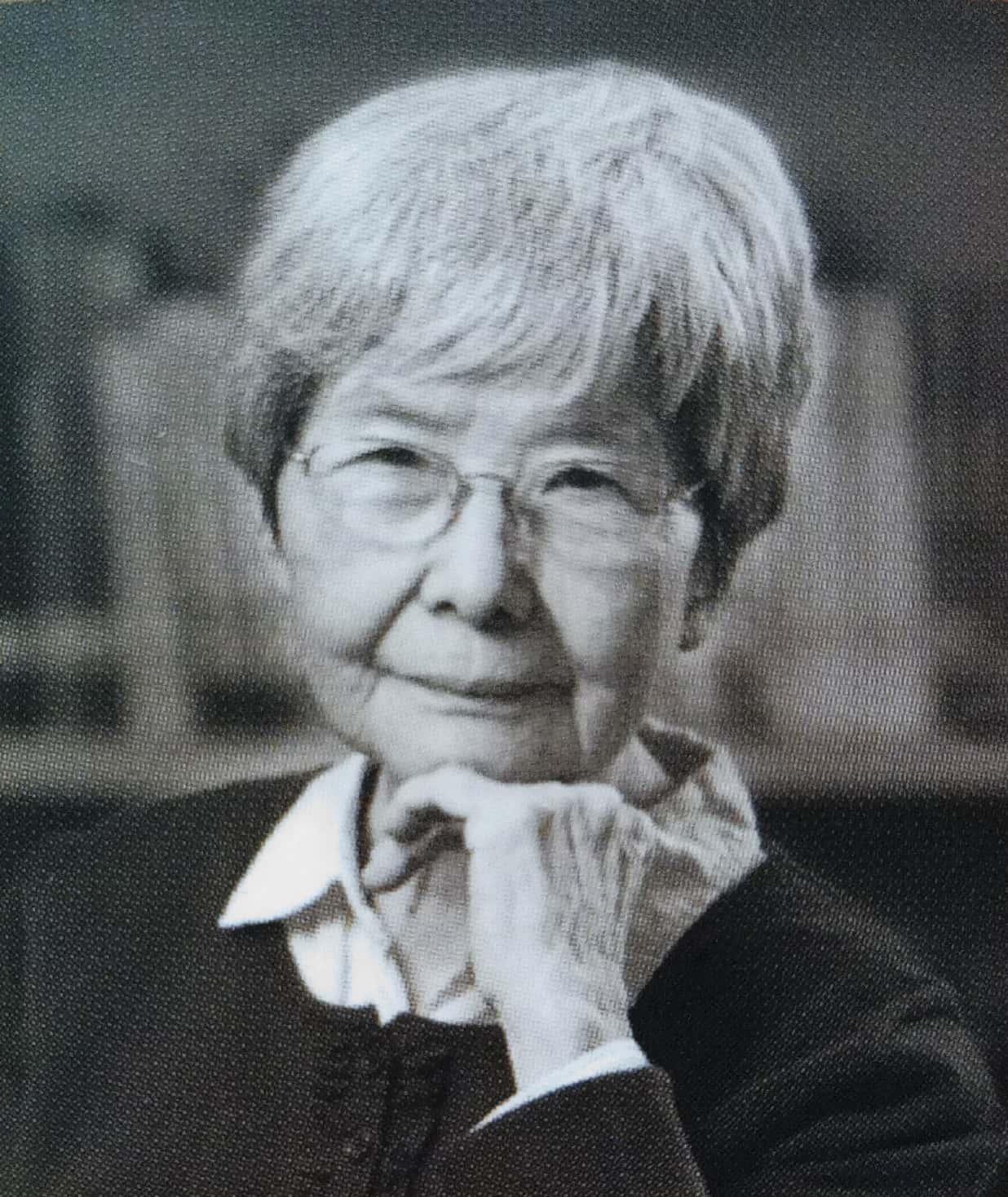
图2.7 樊锦诗先生
(图源: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0,封面图.)
1958年,先生“自作主张”报考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师从宿白、吕遵谔、阎文儒、严文明、李仰松、邹衡、苏秉琦、俞伟超等一众当时国内顶尖的考古大家。1962年,少女时期的樊锦诗先生怀揣着一腔浪漫的热情,选择了敦煌作为毕业前的实习地点,可当时的敦煌却用寒冷和荒凉回应给先生一记沉重的打击。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先生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离开敦煌,返回上海家中休养和整理实习报告。在那一批前往敦煌实习的北大学生里,先生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提前离开的学生,可到最后,这批同学之中唯一一生留在敦煌的人,偏偏还是她。
1963年,先生从北大考古学专业毕业后,被学校分配前往敦煌。在2019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栏目的采访中,先生坦言自己“并没有豪言壮语说我服从国家分配”,支撑着她的是“一个美好的希望,那就是三四年以后,学校会分配新的考古专业毕业生来敦煌,我一定会回到南方,和我的家人,和老彭(先生的丈夫彭金章先生)在武汉团聚”[32]。然而现实是——从1967年先生与相恋多年的大学同学彭金章先生结婚,到1986年彭金章先生主动放弃在武汉大学的任教工作前往敦煌与先生团聚,夫妻二人两地分隔了整整19年。提起丈夫,先生总是十分感激,在访谈里一度直言:“如果爱人不支持,我早就离开了,我还没有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33]这句话或许是身为女性,这位伟大的考古学家在神坛之下最有血有肉的一声感慨。
彭金章先生来到敦煌后,放弃了自己以往商周考古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研究佛教考古。在樊锦诗先生的提议与支持下,彭先生对少有人涉足的莫高窟北区进行了全面的发掘与研究,将莫高窟已编号发掘的492个石窟数(含莫高窟南区的487个石窟和北区的5个石窟)增加到了现如今的735个,更加靠近唐代石碑中“窟室一千余龛”的记载。彭先生撰写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三卷)[34]将莫高窟北区的248个石窟系统划分了类型和功能,填补了敦煌莫高窟研究上的一大空白,得到宿白先生的高度评价。这背后不能不说有着樊锦诗先生的巨大功劳。
1963年,樊锦诗先生服从安排来到敦煌;1998年,先生以60岁高龄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先生离退卸职,又荣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在研究院工作的52年时间里,樊锦诗先生只做了一件事——保护敦煌石窟。宿白先生在敦煌见到樊锦诗先生时,曾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樊先生作为其学生,应该“好好做学问,专心做自己的考古研究,其他事情少管,不能把大量时间耗费在和自己专业无关的事情上”[35]。但是,从另一角度上讲,文物保护与研究的意义又或许并不弱于考古发掘。
敦煌石窟作为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正缓慢但却不可逆转、亦无法阻挡地消失。有关壁画和石窟造像的文物保护问题,“目前尚未出现完善的保存材料和保存工法,有待往后去研究开发的问题也所在多有”[36]。面对这项世界难题,今天人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竭尽所能地维持文物及其所处环境的现状,以尽量减缓它们消失的速度。
“所有的这些努力,为的是让敦煌延缓衰老和消亡,为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石窟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从而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37]——樊锦诗先生在敦煌的半个世纪里耗尽心血所做的工作正是这个。从最初的抢救性保护和修复,与盗贼和当地原住民们斗智斗勇;到接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后,极力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经济开发之间的矛盾。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先生从数字化快速发展的前景里找到了适合敦煌石窟艺术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的新出路——利用不断成熟的数字化技术,既可以真实地留存住敦煌石窟内现有的全部图像信息,又为减轻窟内旅游开发压力而规划的“窟外看窟”创造了条件。“数字敦煌”的设想与实现,是樊锦诗先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极富创造性的功绩,不但对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意义非凡,更为其他所有境遇相似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借鉴。
先生接受毕业分配出发前往敦煌时,苏秉琦先生曾告诉她:“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好好搞。”[38]虽然因困难重重,直到2011年,预计全文将达百卷的《敦煌石窟全集》的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39]才在樊锦诗先生的带领下完成并发表,但它毕竟是国内首部经科学整理的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这卷考古报告“是永久地保存、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推动了敦煌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满足了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在石窟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它为全面复原提供了依据,使之成为可能”[40]。《敦煌石窟全集》首卷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的石窟考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如今的樊锦诗先生荣集一身:1985年获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章;1991年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9年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3年荣获中国公民道德最高奖“雷锋奖”;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2020年5月17日,樊锦诗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凡此诸多荣誉,不胜枚举。然先生常说:“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在写给北大新生的亲笔信中,就她自己所言:“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值得。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无怨无悔。”敦煌于先生而言,正如母亲之于女儿——无从选择,皆是宿命;爱之深切,此生不渝。
或许,抛开神坛之上的种种荣耀与光环,樊锦诗先生的一切身份就只是——“敦煌的女儿”。
八、小结
除前文所述的七位伟大的女性考古学奠基与建设者外,还有如周英学先生、王劲先生、陈丽琼先生、邵望平先生、叶小燕先生、穆舜英先生、禚振西先生、朱非素先生、韩汝非先生、刘莉先生、杨建华先生、滕铭予先生、王全玉先生、吴小红先生、田静先生、秦岭先生、王芬先生、耿超先生……等众多杰出的女性考古学家不能逐一详述。她们在人数上或许远少于同时期的杰出男性学者,但每一位都为我国考古文博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付出与努力。她们的存在让世人看到,考古学需要女性。这些巾帼女将们,正是中国考古学的青史笔墨之下最美丽的风景!
注释:
[1] 容媛,胡海帆.秦汉石刻题跋辑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9.
[2] 东莞市政协编.容庚容肇祖学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8,第428页.
[3] 北京大学考古系资料室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7.
[4] 姜勇.也说游寿[N]. 中国书法报,2020-07-21(005).
[5] 游寿,于莲英.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呼盟的旧石器晚期骨制工具[J]. 北方论丛, 1980(1):94-97.
[6] 王立民.文心雕虫[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3.6,第84页.
[7] 岱峻.一位女学者的李庄经历[J].粤海风,2007(01):38-45.
[8] 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9,第349页.
[9] 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考古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0,第1页.
[10] 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9,第1页.
[11] 梁丽君.文博大家曾昭燏[J].文史天地,2011(09):25-28.
[12] 罗宗真.我与曾昭燏先生的点滴时光[J].大众考古,2014(03):19-21.
[13] 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8,第508页.
[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8,第642页.
[15] 任之恭.何正璜传[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8,第71页.
[16]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何正璜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6,第8页.
[17] 何正璜.西北考察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5.2,第19页.
[18] 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J].说文月刊,1943,(3:10).
[19] 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10,第154-155页.
[20] 蔡昌林.何正璜——20世纪中国联通文博与艺术界的杰出女性[J].美术观察,2010(05):118-119.
[21] 何正璜.何正璜考古游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2,第154-200页.
[22]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何正璜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6,第3-4页.
[2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第131页.
[24] 郑振香,陈志达.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J].考古学报,1977(02):57-98+163-198.
[25] 郑振香.记忆殷墟妇好墓[J].大众考古,2014(04):19-23.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2.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殷墟建筑遗存[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9.
[2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第363页.
[29] 郑笑梅.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63(07):347-350+3-5.
[30]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
[3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9.
[32] 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0,第56页.
[33] 李芳.对话樊锦诗: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J].阅读,2019(32):53-56.
[34]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7.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7.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7.
[35] 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0,第397页.
[36] 泽田正昭著,王琼花译.文化财保存科学纪要[M].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2001.5,第178页.
[37] 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0,第351页.
[38] 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0,第54页.
[39]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8.
[40] 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0,第409页.
图文:杨愫









 重庆考古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