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址概况
观音坡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位于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地处北山佛湾西北1公里的观音坡南侧近坡顶的崖壁上。地理坐标为北纬29°42′48.9″,东经105°42′03.5″,海拔530米。造像分布于长30米、高6.5米的南向崖壁上,崖前地势平坦,前方视野开阔(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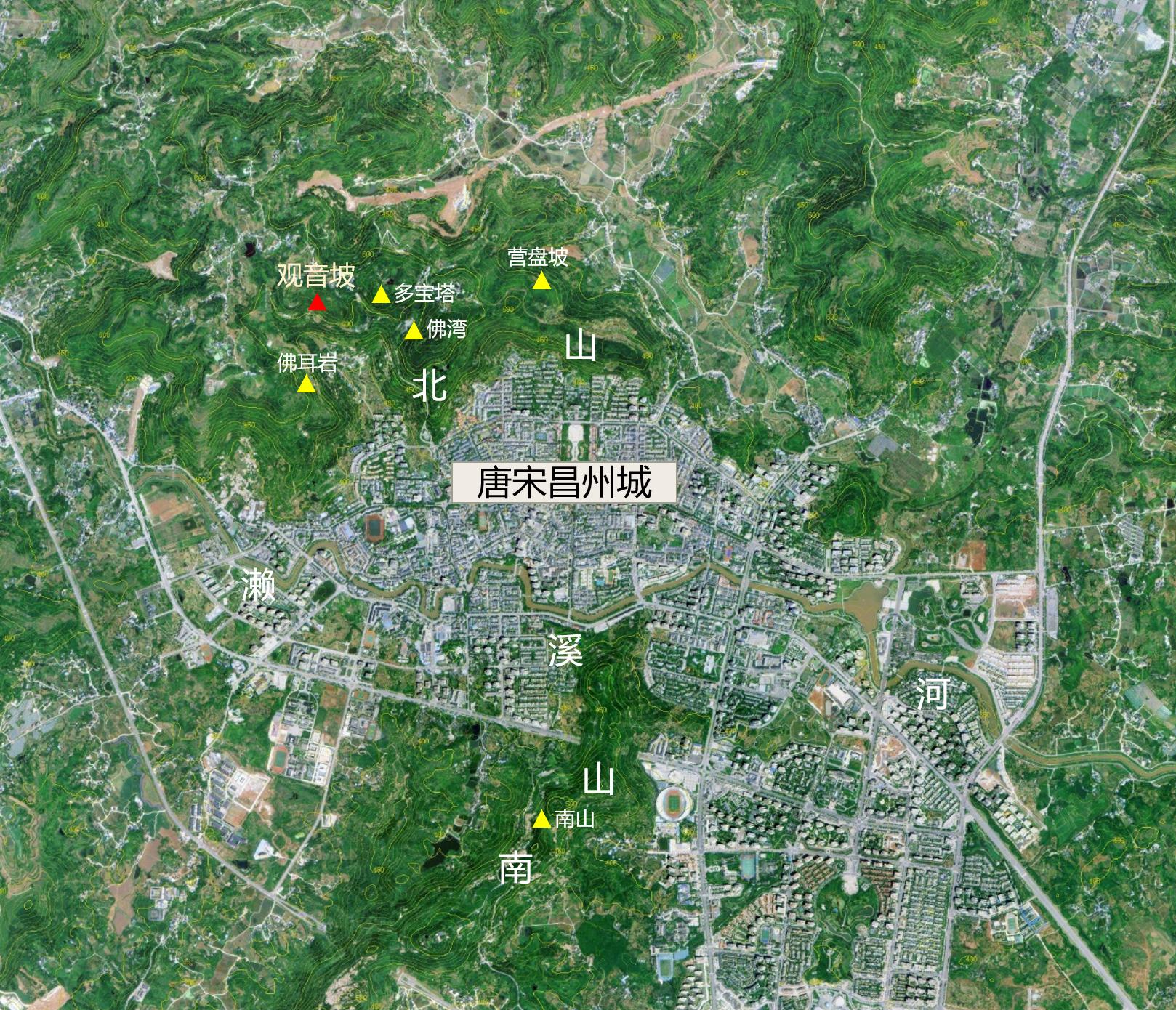
图一 观音坡摩崖造像与寺庙建筑基址和周边造像点相对位置图
关于该地造像情况,大足石刻研究院已撰专文介绍[1],造像开凿于晚唐至南宋,题材主要有如意轮观音、千手观音、释迦牟尼、华严三圣、地藏王、引路王菩萨、天龙八部等。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4年8月—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大足石刻研究院对观音坡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遗址分为建筑基址区和墓葬区,其中建筑基址区位于墓葬区东北部(图二)。

图二 观音坡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发掘区俯视照
二、调查和发掘方法设计
北山石刻文物遗存丰富,分布有唐代的山寨、造像、寺院、道路等,且与昌州城、大足县城关系密切,延续时间从晚唐五代到明清,是开展石窟寺区域系统调查、聚落考古的理想场所,也是探索中国石窟寺考古理论、方法的理想地点。因此,我们以观音坡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的发掘为例,对寺院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
(一)“全覆盖式”调查理念及方法在石窟寺中的应用
“全覆盖式”调查,是以聚落形态研究为目的,通过系统采集特定区域、特定时段的地表遗物,揭示聚落形态的历时性变迁及聚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尽管这种调查方法多用于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但基于川渝石窟寺的特性,这种调查方法同样适用于石窟寺调查。对川渝地区石窟寺进行全覆盖式调查,重点是对石窟寺遗址中的龛窟造像及与之相关的建筑遗迹、墓葬、景观环境和背景环境等进行系统性调查,这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单个石窟寺或区域内石窟群的要素构成、组合关系以及形态变迁。
在这一理念和方法的指引下,我们以北山作为观察的最小单元,对其开展了大范围的全覆盖式调查。通过田野踏查和口述史采访,同时结合《韦君靖碑》等文献资料,在观音坡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周边找到了寨墙、墓葬、水井、采石遗迹等,基本弄清楚了北山不同时期的遗址类型和分布区域,为下一步北山景观的复原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支撑。
(二)依据崖壁和台地方向布设探方
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重庆地区的龛前建筑一般与崖面或台地平行,因此在考虑探方布设方向时,我们没有按照常用的正方向布方,而是根据崖壁和台地的方向来布设,并全程用全站仪高精度测绘。布方方向依据在于:第一,发掘单位与遗迹单位方向一致,符合中国古代建筑群组和单体的规划设计特点,有利于发现重要的线性遗迹现象,避免因方向偏差导致的遗迹断裂误判,提高发掘质量;第二,寻找建筑四至范围时,探方边界可与遗迹方向平行放线,既能充分利用发掘面积又能提高发掘效率,并为后期遗址展示提供更好的效果;第三,探方隔梁方向与建筑方向垂直或平行,探方壁面所显示的遗迹剖面和地层尺寸就是正方向的实际尺寸,无需经过先求得投影再来换算这一步骤,数据更为直观和准确。
(三)“十字探沟”试掘的应用
为快速掌握遗址保存情况,探方布设好后,我们在崖前台地中部开设了南北和东西向交叉的两条探沟,形成“十字骨架”。其中东西向探沟方向与台地平行,横贯台地的东西两端;南北向探沟则与台地垂直,从崖壁下方延伸至下一台地,并将两台地之间的陡坎包含在内。需要强调的是两条探沟均位于所布设的探方内,且保留了探方之间的隔梁,以便全面揭露时衔接(图三、图四)。

图三 “十字探沟”试掘完工照

探沟试掘深度根据遗迹的保存状况差异化处理:在台地中部揭露至最晚一次营建建筑的废弃面,而在台地两端无建筑分布区域,则直达基岩或生土。通过“十字探沟”的试掘,我们初步确认了建筑基址的东西面阔和南北进深以及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为布方的位置和方向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四)从窟前到窟顶的立体勘探模式
石窟寺本体包括龛窟本体和寺院遗址两大部分,龛窟又由龛窟形制、造像、壁画、崖面建筑遗迹、龛前建筑基址、碑刻题记等组成;寺院遗址主要有宗教建筑、生活建筑、生产设施、僧俗墓葬、内部路网、寺产僧田等,因此,石窟寺考古调查和发掘要将这些组成要素统一纳入,考虑其相互关联性。另外,川渝地区石窟寺窟(龛)前建筑形式多样,其显著特点是建筑与石窟(龛)所在的崖面紧密结合,因此会在崖面、窟顶等相接处留下与其相对应的建筑遗迹。据此,我们在不同区域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勘探:第一,在窟前的四级台地上进行调查和试掘,基本确定了建筑遗迹在窟前的分布范围,同时,还在窟前台地上发现了宋、明、清三个时期的墓葬;第二,对崖面进行仔细的辨认与甄别,确认除了两期造像之外,并无建筑遗迹分布;第三,在窟顶做调查勘探,并开设探沟进行试掘,试掘的结果表明窟顶并未分布有建筑遗迹,即表土之下为基岩。通过“窟前-崖面-窟顶”这种地上与地下相结合的勘探模式,进一步确定了主要发掘区域就在窟前的台地上。
(五)全面揭露的关键—隔梁处理与建筑分期研判
通过前期的调查与试掘,主要发掘区域已基本确定,接下来就是对遗址进行全面揭露。在全面揭露过程中,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注意:一是建筑基址一般跨探方分布,在揭露时就面临如何处理隔梁的问题,根据需要,在留取好资料的前提下,可将影响发掘判断的隔梁打掉,但是要注意保存关键柱,除了保存地层剖面,明确层位关系和提供发掘过程中的对照基准外,在隔梁不存的情况下,其还可以供发掘后期的复查和验证。观音坡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发掘过程中,隔梁均未保留,在建筑基址区的东西两端保留了两个关键柱,正是这两个关键柱,为后期的局部解剖提供了对照基准,也为统一地层提供了校验依据(图五)。

图五 全面揭露中的关键柱
二是大型建筑的营建存在多次营建或改建的情况,在建筑朝向和规模体量方面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全面揭露的过程中,一要注意建筑柱网和台基是否发生改变,如果有变化则要考虑建筑分期的可能。如果柱网和台基整体沿用不变,则要注意观察建筑外地面、台基边壁、台面铺设、墙体等结构是否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如果存在,就需要判断是属于同次建筑的不同营建次第,还是属于同期建筑的不同次修建[2]。观音坡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保存了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南宋早期和明代三期建筑,其中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和南宋早期建筑保存情况较差,但我们通过柱网、台基、台基边壁、室内设施等结构,基本把三期建筑的朝向和规模体量弄清楚了,尤其是明代建筑的形制规格已较为清楚。
(六)精准发掘与关键性解剖相结合
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在保证明代建筑完整性的前提下,我们运用了精准发掘与关键性解剖相结合的方式来寻找早期建筑。
一是采用小探坑、小探沟发掘方式,沿着地面已暴露出来的台基边壁、柱础等结构寻找早期建筑的关键节点。同时,利用探针在不破坏遗迹的前提下能快速获取地下信息的特点,在晚期建筑地面空隙处进行了大范围勘探,有线索的地方进行小范围揭露,确认情况并拍照留存资料后立刻回填。通过小探坑和小探沟发掘,结合探针预勘探,找到了早期建筑残存的地面及台基边壁等结构,进一步确定了早期建筑的边界线、拐角点和整体形制结构,进而为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奠定基础。
二是关键位置的局部解剖。其出发点是用较少的解剖发掘面积,获取最全面的早期营建遗迹的准确信息,关键位置主要指早期建筑的四至边角和关键性部位,如柱础、转角等。所以,针对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方法:第一,在没有晚期建筑地面保留的地方实施全面揭露,这一部分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晚唐五代至北宋初的造像基座,出土了兽面纹瓦当和筒瓦等遗物;第二,对早期建筑的柱础、包边等进行解剖,基本明确了早期建筑的营建情况和结构布局等;第三,对早期建筑的垫土进行解剖,这一部分解剖到底,确认了垫土堆积情况。通过这种关键位置的局部解剖,基本弄清了早期建筑的整体布局以及相关地面多次营建关系的明确地层学依据。两种方式结合利用的优势在于能最大限度节约发掘面积,且确保不会破坏未完全揭露的遗迹(图六~图九)。
图六 小探坑、小探沟发掘

图七 解剖包边

图八 解剖柱础

图九 解剖房址垫土
三、发掘收获与认识
(一)基本了解了遗址的形成过程
唐末五代至北宋初,观音坡开始开凿造像,这时期的造像主要集中在崖壁上方,同时期北山由韦君靖主持首先在佛湾开凿造像,历经前后蜀,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摩崖造像点,除了观音坡外,还有佛耳岩和营盘坡等造像点。同时,还修建了龛前建筑,由于破坏严重,目前仅可见一个方形柱础和三段残台基包边,出土了北宋初期的瓦当和筒瓦等遗物,从残余部分结构来看,这时期的建筑大致与崖壁平行。另外,通过我们对台地前方所做的勘探工作来看,这个时候还对台地及前方的坡地进行了平台堆筑活动,堆筑方量近3000立方米[3]。
南宋早期,观音坡继续在崖壁的下方开凿造像,在第1龛有“皇宋绍兴二十四年……伏小六镌”的造像镌记,这不仅明确了镌匠信息,还表明了龛像营建的准确年代,为南宋绍兴二十四年。此外,第30龛和第42龛分别有供养人文志和刘揆的题记,这两个供养人还分别见于北山佛湾137、168[4]龛及北山多宝塔第7龛[5],这三处题记的年代为建炎四年、绍兴四年和绍兴十八年,进一步明确观音坡南宋造像的年代为南宋早期。这个时期龛前也修建了建筑,保存情况较差,可见三个柱础及两段台基包边转角,出土了少量花卉纹瓦当及素面板瓦等遗物,从残存的柱位及包边来看,南宋早期的龛前建筑方向与崖壁和唐末五代至北宋初的建筑有较大的角度偏差(图一〇)。

图一〇 南宋初建筑基址
到了明代,早期建筑毁废,对部分区域地面进行平整后,继续修建了寺院建筑,这一时期的建筑保存较好,可辨前殿、后殿、左右侧殿和天井等结构,除后殿保存不理想仅见台基包边和踏道外,其余部分均保留了石铺地面、柱础、排水、台基包边等结构,后建筑毁废后遭到填埋,形成了建筑废弃物堆坑,掩埋了大量建筑构件(图一一)。同时,在台地西侧营造了僧人墓园,可见两座形制结构不同的僧人塔墓。而在清代,龛前主要成了俗人埋葬区。

图一一 K1清理照(南—北)
(二)初步弄清了明代寺院的布局结构
观音坡明代寺院由唐宋时期摩崖造像区、寺院建筑区和僧人墓葬区三部分组成,是一处布局结构相对完整的石窟寺遗址。明代建筑由前殿、后殿、两侧配殿和天井等组成。其中前殿由台基、包边条石、铺石地面和柱础等组成,台基残存部分呈方形,包边由方形条石垒砌而成,底部为长条形石块平铺的土衬石,其上为陡板石,陡板石上铺有阶沿石,阶沿石外侧为排水沟;铺石地面由长方形石板横砌或顺砌;残存东西一排四个柱础,形制均为上下两层,上圆下方,根据柱位可复原为面阔三间,进深不详。后殿由台基、包边条石、踏道、排水沟组成。台基平面呈方形,其前侧、左右两侧均由石砌包边,均用条石错缝平砌,踏道位于左侧台基前方,中央有三阶踏跺,左侧有垂带,右侧垂带无存,顶面地面无存。左右两侧配殿由铺石地面、柱础、排水沟等组成,铺石地面用长方形石板横铺或顺铺,柱础均为方形,前方连接有墙板地袱石,台面后部有阶沿石,阶沿石外侧在基岩上开凿有排水沟。天井用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石板铺地,其后部和右侧均有排水暗沟,两壁和底部均用石板砌筑,顶面铺有石板,后部用石板垒砌包边。建筑整体保存较好,进一步丰富了川渝地区石窟寺建筑形式的案例(图一二)。

图一二 明代寺院布局结构
(三)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僧人墓园
僧人墓园包含了墓园地面、墓塔、地宫、拜台、塔亭基址等,是川渝地区发现的少见的保存较完整的明代僧人墓群。墓园后部保存较好,用石板铺地,石板均为方形,或横铺或顺铺。后侧及右侧保留有围墙,均用方形条石错缝垒砌而成。墓塔由基座和塔基两部分组成,塔身部分已不存,基座残存由方形条石垒砌的包边,其下为土衬石,其上平铺石板;基座中部放置方形塔基,上承六边形方座,两面转角做成微曲兽足状,上饰卷云纹。地宫形制有多室和单室两种,其中多室墓地宫平面呈凸字形,由拜台、封门、墓室、棺床四部分组成,摆台位于墓室前方,平面呈方形,两侧竖砌石板作拦板,中部放置一方形碑基座;封门用方形石板封堵,底部为长方形基石;墓室分为后室和左右侧室,中间以过道相连,其中后室中部为须弥座矮棺床,而左右侧室为二层低坛,其上均放置灼烧过的骨殖,每个墓室均以石墓门封闭,相似形制的墓葬还见于大足宝顶山游客中心基建工地古墓群M13[6]和荣昌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M4[7]。单室墓地宫平面呈六边形,均用条石垒砌而成,南部整体坍塌较北部矮,墓壁石板向外推出形成壁龛,墓底用石板铺成,中央放置一六边形须弥座仰莲台,座上承托一圆形仰莲台,其上放置一带盖石缸,类似的墓葬也见于荣昌报恩寺塔墓群的M1[8]。塔亭基址由地面、柱础和墙基三部分组成,地面由长方形石板平铺而成,整体略高于墓园地面高度,南部坍塌下沉。残存8个方形柱础,根据柱础的分布规律推测塔亭应为方形。墙基残存北部和东部外墙基,用长方形薄石板拼接而成,墓塔上方覆盖塔亭的案例可见于安岳木门寺无际禅师塔。此次清理的僧人墓园对于认识川渝地区明代僧人墓葬结构、丧葬习俗和墓上建筑等具有重要价值(图一三)。

图一三 僧人墓园整体(北—南)
(四)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寺院遗物
本次发掘出土器物以建筑构件、石质造像残件、陶瓷器为主,并出土少量铜铁器。其中建筑构件又分为石质和陶制两类,石质建筑构件包括望柱、栏板、鸱吻、脊兽等,陶制建筑构件以泥质灰陶为主,主要有瓦当、板瓦等。石质造像主要为佛、菩萨、弟子等头像及造像基座等。此外,陶器以泥质灰陶和泥质黄褐为主,器类有烛台、盏、砚台、器盖、器钮和造像残件;瓷器以褐胎为主,器表施白釉、黄釉、黑釉、酱釉,器类有碗、罐等。铜器有铜钱、铜簪,铁器主要为棺钉。
这些遗物对于认识川渝地区的龛前建筑形制和整体布局具有重要价值(图一四~图一七)。

图一四 出土瓦当

图一五 出土石造像身体残件

图一六 出土陶鸱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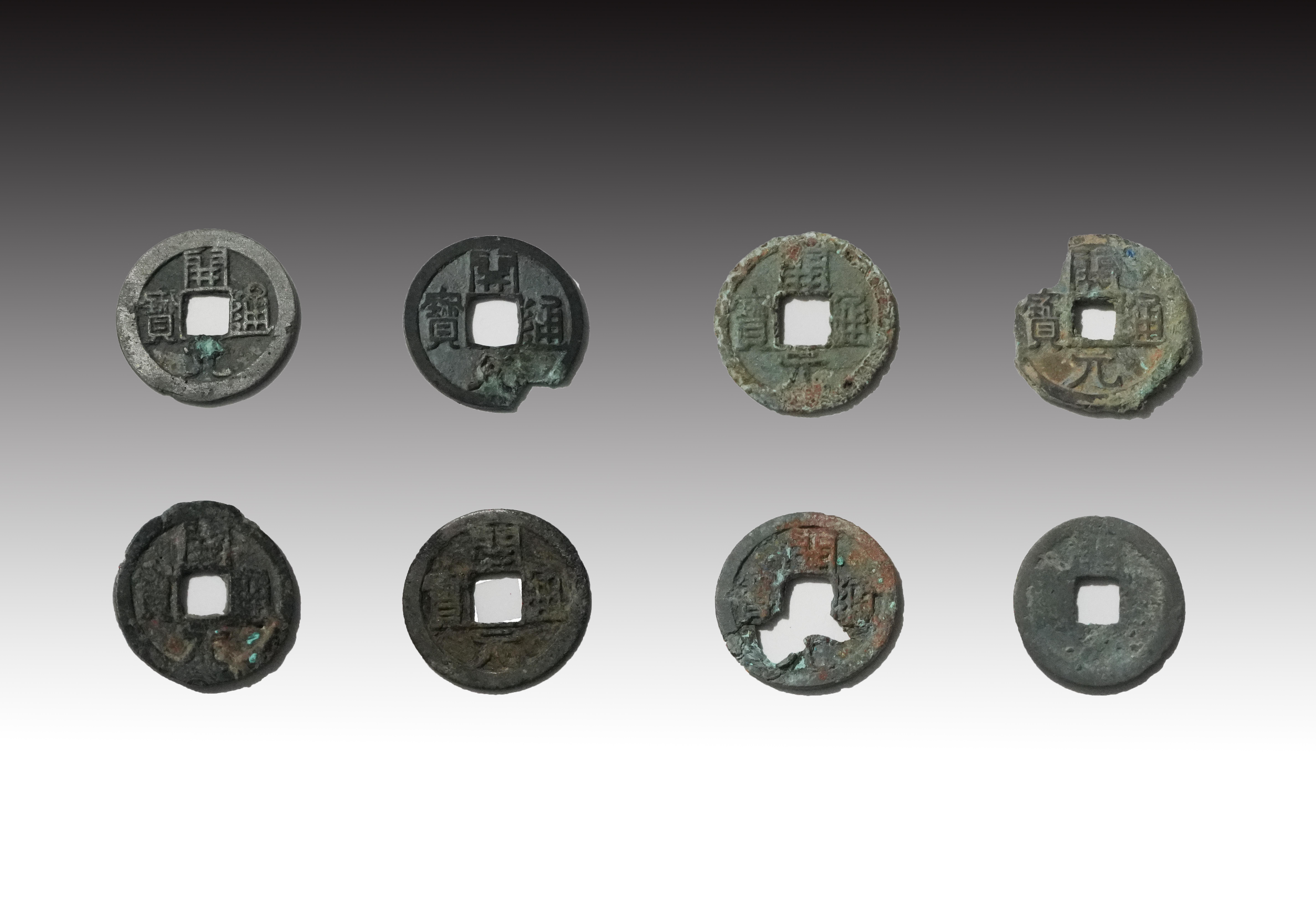
观音坡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是集摩崖造像、龛前建筑基址、墓葬于一体的布局结构相对完整的石窟寺遗址,特别是龛前建筑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川渝地区石窟寺建筑形式的案例,是认识北山石窟寺基本构成要素的重要案例。同时,多期建筑的叠压也为弄清楚北山造像和寺院发展沿革提供了重要线索。
注释:
[1] 大足石刻研究院:《北山观音坡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待刊。
[2] 汪盈:《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设计》,《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年第8期。
[3] 此方量为按面积及深度的估算方量,并非准确数据。
[4]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编《大足石刻铭文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30、73页。
[5]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编《大足石刻铭文录》,第445页。
[6] 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大足宝顶山游客中心基建工地古墓群清理简报》,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大足石刻艺术研究会编:《大足石刻研究文集(5)》,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449-453页。
[7]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荣昌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考古发掘简报》,待刊。
[8]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荣昌区文物管理所:《重庆荣昌区报恩寺僧人塔墓群调查和清理简报》,待刊。
文稿:张春秀 牛英彬









 重庆考古
重庆考古